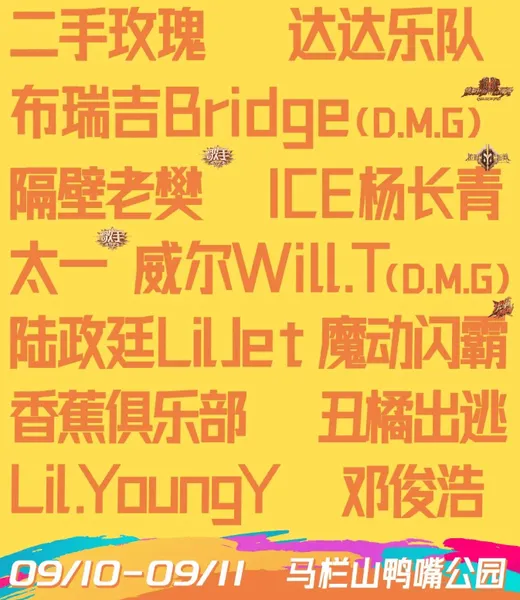今年端午节期间,一场集合广州交响乐团青年古典音乐家和大湾区优秀现代舞者的创意演出——“乐动·舞界 现代舞×室内乐:拉威尔与皮亚佐拉”即将于6月22-23日在星海音乐厅首演。
经过多年探索,星海音乐厅在成立25周年之际,全新推出“乐动·舞界”品牌系列,在舞蹈与音乐领域打造跨界原创节目。此次新品牌首秀,迎来四位来自大湾区的青年舞者,与广州交响乐团常任指挥景焕及十多名乐手共同呈现。舞者和乐者将以他们独特的艺术语汇,展现跨界激情,将耳熟能详的古典与现代音乐以全新视角呈现,也彰显了湾区合作的新视野。
演出开始前,舞者毛维(香港)、李拓坤(香港)、陈艺洁、沈盈盈在广州聚首,开启了密集的编排创作。他们抛开自身过往经验与预设标签,用自己潜藏身体内的声音与拉威尔、皮亚佐拉展开对话。南都记者在开演前,于排练现场与四位舞者面对面,让我们一窥舞者们如何用身体跃出乐章。
此次“乐动·舞界”首秀演出选择的曲目是拉威尔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奏鸣曲》和皮亚佐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
“小提琴和大提琴奏鸣曲”是拉威尔为纪念德彪西逝世而作,他曾这样评论这部作品:“我认为这首奏鸣曲在我的生涯进展中画出一个转折点。”作曲家通过两把琴弓塑造出了一种尖锐的紧张感,作品中主题材料被高度提炼,贯穿在各个乐章中。
另一首曲目则充满南美风情。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语义为“好空气”,有“南美巴黎”之称。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被誉为“探戈音乐界的巴赫”“阿根廷探戈之父”。他在探戈中注入了古典音乐的严谨精致,在古典音乐间注入了探戈的无限激情。皮亚佐拉创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即探戈版《四季》,借“四季”之名,描绘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丰富多样的生活场景。探戈音乐的独特律动和精神气质,在本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拉威尔的二重奏中,仿佛能看到人们在时代浪潮下翻滚前进,个体与回忆之间产生共鸣,展现出一个万花筒般的“魔方记忆”;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中,舞蹈将充分展现音乐的复杂性与多层次,不同情绪被融合,破解和重组,呈现出一种拉扯的质感。
在编舞时,李拓坤会去了解作曲家的时代背景。“拉威尔的音乐很’新’,他的高音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刺耳,但他其实是在传递那个时代的信息。它的创作背景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你会听到工厂的敲打声,机械的运作声,这也是作曲家的灵感来源。”
另一首皮亚佐拉的《四季》中有许多探戈的元素,舞者们编排时也会尽力去贴合作曲家当下的的情绪。毛维说:“南美洲的四季跟我们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和我们耳熟能详的那首《四季》不同,皮亚佐拉的《四季》让我更能感觉到南美洲人热情的生活态度。”
“《四季》的那种跃动感和节奏感,它会给我一股冲劲儿,那种热情奔放的感觉,会让我自己很想在里面打开我自己,去接受这个能量。”陈艺洁说。
身体的直觉给了沈盈盈更多的灵感。“我在听他们的音乐的时候,很自然地有一种律动感,我们不用专门为了一个节奏去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只要跟着音乐律动,很自然地产生出动作。也许这个动作很简单,并没有说很炫技,很浮夸,但是它能完全符合这个音乐的质感。”
在四位年轻舞者的演绎之下,拉威尔与皮亚佐拉的音乐流转于舞台,时而激烈奔放,时而抒情柔美。在这场别具一格的创新演出上,音乐将被“看见”,舞蹈将被“听到”,多元艺术在交响乐演奏厅里碰撞,交融,新生……
访谈
南都:作为舞者,你们如何用身体去诠释拉威尔和皮亚佐拉的音乐?跨界合作的创作模式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新体验?
毛维:这次的编创是建立在一个已经确定的音乐上。在以往的经验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以音乐为主导,而是以身体为主导去创作,再拿音乐去配合我们的动作。这一次恰恰相反,我们很少以音乐为主去编排。我们很努力地去感受这个音乐带给我们的情绪。每个章节的转折,情绪的高低起伏,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去配合,同时又怎样去发掘我们身体不同的可能性,这很有趣,这是突破也是一个挑战,让我们每天都像打鸡血一样,拼了命地在碰撞想法。
陈艺洁:这一次编舞虽然是四个人联合编排,但实际上也是我们四个人的个人化的旅程,有些人听到很轻快的音乐,或者很强劲的音乐的时候,身体会有一种动感,这种东西其实是来自于身体的自发性,它是你曾经个人所有经验的结合和输出,是来自于你个人的历史,个人的身体经验。
南都:对于这一次跟广州交响乐团、跟指挥家景焕的合作,你们有何期待?
李拓坤:在正式开始编排之前,我们去参观了乐团的排练。我看着指挥家的手臂就像在飞舞,一停一顿,一起一拉,在那一刻就已经像舞蹈了,给了我很多灵感。如果乐手们聚集的能量这么强的话,我们的编舞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准,才能和乐手配合到一起,将演出的效果推到最完美,这是我当时那一刻首先想到的事情。
沈盈盈:跟广州交响乐团这么大的团队一起演出,是我们很幸福的时刻。现场伴奏是存在随机性的,你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这个就很考验我们排练磨合的程度,以及我们临场的发挥。
陈艺洁:我也会很好奇现场的及时性的交互,现场音乐和演员之间的呼吸感,实际上是一种能量的流动,我们的身体、服装、道具、灯光,甚至所有的观众那一刻会产生什么样的能量对话,这是我很好奇的。
毛维:我们四个其实一直都认识,所以当星海音乐厅邀请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大概有个概念,知道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东西。这次我们都尽可能地把自己过去的一些编创经验放下,以一个全新的状态去互相配合。
我们编排的时候也在不断地思考舞蹈的音乐性和演奏的音乐性,达到这个层面上的和谐,是我们很努力想做到的。从室内乐、古典乐,到现代舞的编排、身体的呈现,这种结合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也很感谢星海音乐厅的信任,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
南都:从你们的个人经验出发,你们是如何成为舞者的?舞蹈给你们的人生带来了什么?
李拓坤:小时候是我爸爸主动送我去跳舞的。当时我对跳舞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爸就忽悠我说你是去学武术的。去了以后,老师果然是教一些中国古典舞的技术技巧,看起来很像武术,我就把它当武术练了。当我真正地进入到中专,和老师系统地开始我的舞蹈训练生涯的时候,我真正地爱上了舞蹈。因为舞蹈给我更多的是一种通过肢体表达自己的情绪。对于我来说,肢体的动作能影响我的心理,身心是互相影响的。舞蹈能帮助我将一些生活中的压力和情感,通过肢体的动作释放出来。对我来说舞蹈是我去感受这个世界、连接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
沈盈盈:我的学舞之路比较传统。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我爸妈就说,那要不就送她去学武术,要不就送她去学舞蹈。后来他们想女孩子还是学舞蹈比较好。就这样一路在机构学,直到2007年广东舞蹈学校来招生,我就考上了。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现当代舞。当时就觉得现当代舞是我的一根救命稻草。因为如果继续跳中国舞的话,也许我会变得很不自信,很苦恼。当时我觉得现当代舞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让我真的在舞蹈当中找到了自信,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舒服,很享受那一刻。
研究生阶段我到了台湾,再后来考到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真正成为了一名舞者,还是很享受舞台、享受谢幕的那一刻,对舞台的那种迷恋,每次都像是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会抛弃掉你日常生活中琐碎的烦恼,很沉静地享受那一刻,我觉得这种心理状态可以让我一直走下去。
陈艺洁:我其实是没有“舞蹈”概念的,我更愿意称它为“运动”。我从小就很多动,完全停不下来。我现在坐在这里,其实内心一直在嘣嘣嘣嘣嘣。我经历过了中专艺校六年,直接进入到广东现代舞团,之后再去到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我很早就进入到了舞团的这个语境里面,但那个时候对我来讲,舞蹈是一种创作的语汇,我在用我身体去呈现一种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我用身体在认识我自己和认识周边,认识我正在经历或者发生一切的过程。它是一个媒介,它是一个非常充实的媒介,甚至高过语言的媒介。对我来说,所有语言都有局限性,无法完整描述出我内心丰富的,既抽象又细碎的感受,对我来说身体比语言更加敏锐,这也是为什么我迷恋身体去运动的原因,我比较喜欢通过身体去探索未知的东西。舞蹈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提出问题”。对我来说,创作的过程是重新生成一种认识、解读世界的角度或是方式。这个过程是一种无限循环的疑问,我们在里面无限循环地追寻,这个寻找答案的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
毛维:我小时候学跳舞也是被我妈骗过去的。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我扒着门哭着说,我不跳舞,男生不可以跳舞,同学会笑我的。我坐在地上哭,就这样开始学中国舞,后面阴差阳错有机会到香港演艺学院读书,接触了现当代舞。这十多年下来,我觉得创作的核心不是为了去做一个多么好的作品。而是把创作者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在舞台上以一个艺术作品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它的背后是有一个清晰的逻辑和思考的,它建立在一个真实的情感和经历上,这个真实性是具备很大价值的。这也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
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实习生 康紫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