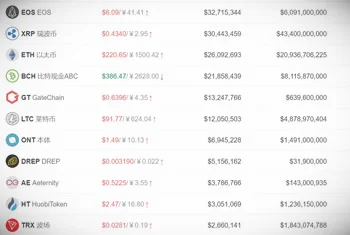
作者:管春平
相隔二十多年后,又看《智取威虎山》。演出结束了,泪眼朦胧的我和其他观众一起向谢幕的演员们再一次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份感激是由衷的,那份激情是由衷的,那份荡气回肠的怀旧体验是从未有过的。
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我,整个童年都浸润在一个激情昂扬的时代,我的感情世界就是在诸如《智取威虎山》这样的高昂旋律中孕育和成长的。虽然那个时代留给历史的是一页灰色的记录,留给人们的是一段苦涩的记忆,但在我童真的世界里,《智取威虎山》留给我的却是如今的孩子们在现代影视剧中难以寻觅的纯真和激情。原以为经过二十多年岁月的磨砺,那份纯真和激情已经尘封,却不曾想,当我二十多年后再看《智取威虎山》,那熟悉的旋律,熟知的人物,陡然又唤回久违了的情感体验。当泪水悄然蒙住双眼的时候,我才知道,在我的情感深处,关于纯真和激情的记忆早已刻骨铭心;我才知道,原来回望岁月,可以让人如此的激情难抑——有些酸楚,有些痴迷,有些心痛。
《智取威虎山》
初看《智取威虎山》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我大约六、七岁。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在每年少有的几次电影放映队下乡的时候,跟着这支放映队连续几天在方圆十里以内的几个村子里看同一部电影。虽然每天晚上要往返十几里山路,而且看的是部同样的电影;虽然因为每晚十点多钟回家吵醒了睡梦中的父母而受到责说;虽然是那种把一块白布挂在两根竖起的木杆上的简陋的露天电影;虽然看电影的座位只能是自家带的木板凳或是随便找来的一块石头或砖块,而且有时因为人多不得不坐到银幕的反面去,字幕是反着的,影像是模糊的……但那块普通的白布上所演示出的好看的故事、好听的音乐和可爱的好人、可恨的坏人,以及永远都是好人战胜坏人的美好结局,对于文化生活贫瘠的农村孩子来说仍然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所以,不管天冷天热,不管刮风下雨,不管父母如何责说,不管看银幕的正面还是反面,我们都乐此不疲。每天晚饭后成群结队地上路,夜半时分心满意足地回家。现在想来,当年简陋的露天电影对于农村孩子的吸引力绝不是拥有立体音像效果的现代影剧院所能企及的。
那时候,我也是一个小电影迷,只要放映队下乡来了,总是像影子一样跟在大我六岁的哥哥后面走东村、窜西村。哥哥将我视为“包袱”而不愿意带我,因为带上我他就多了一份责任,就不能像别的男孩子一样撒开脚丫子疯跑。我用尽浑身解数软磨硬泡,哥哥想甩也甩不掉,父母想拦也拦不住。
《智取威虎山》
《智取威虎山》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那些身披白色防雪衣的解放军战士在那白皑皑的林海雪原上滑翔飞奔的英姿,给了我终生难忘的美感。这部戏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苦大仇深的李勇奇对解放军战士由误会为土匪到认定为救命恩人的那段戏。当李勇奇饱含深情地唱出:“亲人呐——”三个字时,我被感动地哭了:原来只有解放军才是专门为受苦受难的人报仇雪恨的,他们太好了,太可爱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也没有读过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智取威虎山》启蒙了我对那些“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解放军战士由衷的敬爱之情,直到今天不曾改变。我曾经梦想长大后成为一个“最可爱的人”,也曾经梦想嫁给一个“最可爱的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切都未能如愿,而这也使我的生命中多了一份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连续看过七八场《智取威虎山》后的一天,哥哥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顶带红五星的绿军帽戴在头上,在我面前有板有眼地唱起来:“我们是工农子弟兵”虽然那时的哥哥长得又瘦又小,我总笑话他细脖颈上顶着个大脑袋,像个拨浪鼓,而且那顶军帽比他的脑袋还要大出几号,但那一天我丝毫没有觉得哥哥的形象滑稽,反而发现他比以前高大英武了许多。以前我也总笑话哥哥唱歌五音不全,可他那天唱的那一段却让我觉得那么优美动听,我上前拽住哥哥:你教我唱,我也要唱……随着岁月的流逝,哥哥长高了,壮实了,但他西装革履的形象在我心中却再也没有了当年那顶绿军帽所赋予的英武之气了。哥哥在我心中留下的最美的形象,就是他当年唱“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时候的形象。
《智取威虎山》
坐在旁边的一位老者喃喃的感叹声将我从回忆中唤回:想不到快三十年了《智取威虎山》还拥有这么多的观众。我留意了一下,偌大的剧场几乎座无虚席,观众多是一些稳健的中年人和鬓发斑白的长者。与其他演出场合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追星族的喊叫声、口哨声,没有献花者,观众们给予演员的只是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不知道这些演员们是不是也是带着对这部戏难以忘怀的情愫来演出的。他们的表演声情并茂,逼真、传神。英雄的杨子荣、勇敢的小常宝,感染着每一位观众。
回家的路上,我久久地沉浸在那份久违的情感中不能自拔,那种难以言传的感受让我一次又一次的模糊了双眼。
然而,马路两侧大酒店、夜总会门前五彩的霓虹灯,却无情地把我的情感拽回到现实世界中。我闭上了眼睛。那一刻,我的眼睛、我的心灵都拒绝霓虹,拒绝现实,我只想在那份久违的情感中再沉浸一会儿,再感受一次。因为我知道,这种沉浸不可能长久,这种感受不会常有。
又看《智取威虎山》,我一夜无眠。
(《金沙滩》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