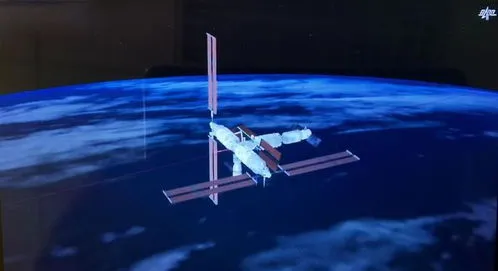△《大师和玛格丽特》剧照。图/乌镇戏剧节
「在今天这个小说里,面对这样一个载体,什么是救赎、勇敢、爱?那些在年轻的时候觉得离我很远的话题,好像离我更近了,更急迫了。」
人类三四百年以来对于世界乌托邦的构想和实践,在上世纪风起云涌的国际局势变换之中宣告失败。
(资料图片)如何想象未来生活,有没有另一种社会建构的可能性,真正的救赎又要从何处找寻,无疑成为当下横亘在我们所有人面前、无法摆脱的重要命题。
12月初,新青年剧团创始人、独立剧场导演李建军将自己的最新戏剧《大师和玛格丽特》带到第九届乌镇戏剧节首演,这也是李建军今年做的唯一新剧。
本剧改编自前苏联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一位被称为“大师”的作家离奇失踪,他的情人玛格丽特备受煎熬。此时,魔鬼撒旦降临,将这里带入末日。绝望下,玛格丽特与魔鬼交易,变成女巫。变身后的玛格丽特焕发出强大的力量,她飞到空中,救出大师,一起飞向理想之国。
这个故事被“大师”写进日记。21世纪,日记被一位天使得到。为了查证日记的真实性、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否到达了理想之国,天使决定穿越回那个时代,寻找答案。
《大师和玛格丽特》剧照。图/摄影师 塔苏
同样通过实时影像和数字影像参与戏剧场面叙事的,还有李建军去年在乌镇戏剧节首演的《世界旦夕之间》。
该剧改编自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同名电影,利用绿幕抠像的技术表现手法,通过“三重虚拟世界”的搭建、交叠和错乱,弥散出上世纪60年代冷战背景之下人们对于现实与未来的恐惧和希望。
《世界旦夕之间》剧照。图/摄影师 塔苏
此外,因疫情被迫取消的《美好的一天》原计划也将作为YOUNG剧场“在地计划”的首部委约作品,在元旦期间呈现给上海的观众。从2013年开始,李建军在作品中引入“素人剧场/凡人剧场”概念,试图通过大量素人演员的起用,探寻普通人与舞台的隐秘联系,解放普通人的媒介表达权利。
《美好的一天》剧照。图/摄影师 李晏
在现代性、存在主义式的命题之下,思考自己与时代的关系,是李建军诸多戏剧作品的共同脉络和主题。
《世界旦夕之间》的结尾,当自己所处世界即将幻灭的时刻,主人公施蒂勒提出一个问题:“真的存在一个终点吗?所谓幸运快乐的生活,又是真实还是虚幻呢?”
在《大师和玛格丽特》这场奇幻、迷离又饱含力量的穿越之旅中,李建军打碎了布尔加科夫营造出的乌托邦,转而给所有中国观众,也给自己一个暂时性的答案:“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失去太阳,故事已经讲完,明天却还未到来……我知道明天不只属于我自己,此刻我们站在一起。”
李建军,独立剧场导演,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2011年创立“新青年剧团”。近年来,他的系列作品因其批判性的文化立场和对剧场美学的探索而受到广泛关注和争议。
以下是新周刊与李建军的对谈:
跟中国的观众对话
新周刊:目前《大师和玛格丽特》这部文学作品已经在世界各地创作出了好几个戏剧版本,为什么选择现在将它带给国内的观众?
李建军:在我的导演工作过程中,肯定有很多很想去触碰的题材,这两年我对经典改编比较感兴趣,原因有很多。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疫情之前,我的戏比较偏重实验,基本上在一些国际戏剧节上演出,国内的演出相对比较少。疫情开始之后我们出不去了,开始有一些国内巡演的需求,面对的更多是中国的观众。
中国观众可能有一个欣赏习惯,他们会对于名著、对于故事性有更多的需求。选用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文本,这样观众更容易认知。于是,疫情之后,我开始选择用一些经典文本来跟国内的观众对话。
《大师和玛格丽特》电视剧剧照。
新周刊:您以往的好多作品,比如说《美好的一天》《变形记》《世界旦夕之间》,都能非常直接地让观众明白你想表达的内涵。这次您开始用一种哲学式、隐喻式的方式创作,算不算您创作风格上的转变,之后会不会使用更多类似的表达方式?
李建军:我暂时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本来在布尔加科夫的小说里边就有很多隐喻、跟现实的一种对应关系,所以在改编这部经典的时候,文本会带来一些限定。当然你要跟今天中国的观众讲一些话的时候,可能也不适合用非常彻底的方式去讲,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小说带来的,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命题带来的一种方式。
《世界旦夕之间》剧照。图/摄影师 塔苏
用一种时间刺穿另一种时间
新周刊:看过《大师和玛格丽特》原著小说的观众在进入剧场之前应该都能意识到,这部小说并不容易改编。它打破了陈旧的时空概念和透视法则,多线叙事并行、交错,文字中很多关于撒旦、女巫的描写也很难视觉化。您在改编、导演这部经典名著时,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李建军:最大的障碍就是,就像你所说的,小说中观众根深蒂固的经典桥段、一些脍炙人口的场景,比如玛格丽特飞起来,把莫文联的大楼砸掉……在舞台上其实都是比较难以呈现的。在排练之前,我研究过一些其他版本的舞台剧的改编,在我的内心没有一个做得成功的版本,都没有办法媲美文字阅读时带给我们的想象快感。
所以把这本小说放到舞台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导演过程中,我一直要去处理这个问题,不能直接把文字中描写的画面照搬到舞台上,此路不通。最后我的方式还是从它的表达内核出发,用舞台的语法去讲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大师和玛格丽特》剧照。图/摄影师 塔苏
新周刊:是不是相当于在文本的故事性和您作为戏剧导演的理念输出之间,做了一个平衡?
李建军:是的。对于所有的戏剧导演来说,如果你用一个现成的剧本或者小说进行改编,这些小说或者剧本都是一种素材,是需要你去借题发挥的。你排这个戏是讲给此时此刻的中国观众看的,它讲的不是一个俄罗斯的故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
怎么用一种舞台的语言把素材变成现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命题,所以在这版改编里,在舞台上制造奇幻的视觉场景,就变得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遵照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去选择使用何种舞台语言。
开始做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布尔加科夫的忠实读者想看的是小说前300页的撒旦的故事,但是在这版改编里,它都变成了一种背景,那些奇幻的场面都没有了,所以我在导演的过程中会有一种拉扯,担心观众对我的改编失望、不满。
在创作中,这其实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要遵循你对这个剧的改编理念,你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要向观众说什么,继而去构思整个舞台,同时又要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是这样的一种辩证关系,里面有非常大的拉扯。
《大师和玛格丽特》剧照。图/摄影师 塔苏
新周刊:您认为这部戏里的哪一幕、哪一个从小说文本到舞台形式呈现的处理,是最恰当的?
李建军:任何形式都是从一种理念生发的,这个理念关于我们今天的现实处境和过去的那一段历史的相互映照关系。在两个时间的互相映照中,用一种时间去刺穿另外一种时间。
实际上我们很多舞台构思都是由此生发的,比如戏里面的撒旦是一个现代人;我们把很多影像做成30年代的黑白影像,其实还是在用一种穿越的思路。
但里边一定有很多的现代元素,包括演员的跳出,走到前面用演员的视角向观众说“如果我活在1930年代的莫斯科,我会怎么样”?再比如说我在舞台上设置了化妆间,是我们做舞台剧的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化妆间。在化妆间里,我是演员,我是生活在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我要演一个1930年代的莫斯科人,他有一种时间的映照关系。
从语言到舞台形式都是从“你要向今天的观众讲话”这样一个理念生发出来的。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决定,都是从这儿出发去考虑,放到里面去,判断它恰不恰当、适不适合。它不是一个现成的工具,是需要你去发明创造的。
回到困苦当中,没有别的路
新周刊:原著中虚幻式的、宗教般的救赎结局,被你改掉了,大师和玛格丽特拒绝了撒旦的邀请,并没有一起飞往理想之国。这样的结尾改编,你是出于什么考虑?
李建军:布尔加科夫死于上世纪40年代,他去世以前生活在一个很困苦的环境里,他在困境里去写作、去表达。在他去世以后,我们的历史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前苏联也解体了。后来的历史是布尔加科夫不知道的。
在布尔加科夫生活的时代,他所想象的救赎和安慰是宗教式的,所以在他小说结尾,主人公到达了宗教般的彼岸,这是他们文化中的一种救赎方式。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虚无的结局。
《大师和玛格丽特》剧照。图/摄影师 塔苏
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经历了布尔加科夫逝去之后的诸多历史,而且在我们文化里没有那样一个宗教式的彼岸,那我们在现实中应该怎么看待那样一种宗教语言?
事实上,没有别的路,没有一个可以飞出去的地方,没有那样一个所谓的乌托邦,没有那样一个虚幻的彼岸。我们真正的救赎之路就是回到我们的现实之中,只有回到我们的困苦、回到我们过去的理想中,去经历那样一段历史,一步一步地克服困难。往前走,这就是救赎之路。
新周刊:之前您做的很多现实主义作品,会去做很多田野调查、深入采访,比如您做《带电的火花》时,就跟着主角马建东去了他的家乡,跟他一起生活。这次改编这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创作方式上会不会跟之前不太一样?
李建军:在我的创作经验里,其实每一部戏最后呈现的样子、观众感受到的样子,是由你触碰的那个问题、你想讲什么故事、你给谁看来决定的,它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风格问题。
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带电的火花》,它是给线上观众看的,不会在现场演出,所以,它做成了那个样子。而今天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在乌镇戏剧节这样一个1000多人的场子里演的,这是一个原因。
《带电的火花》剧照。图/摄影师 塔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我想表达的这个事儿(用一种时间刺穿另一种时间)跟一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碰撞的时候,它会开出什么东西,我不存在一个预设。最酣畅淋漓的情况是不要给自己框定一个风格和方法,它自然会长出来。我的经验都是这么工作的,回看以前的作品,好像都是这么出现的,我也没有想到它们最终呈现出来会是那个样子。
找到真正的痛点
新周刊:《大师和玛格丽特》这部戏您用的都是专业演员吗?
李建军:是的,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有过演出经验的。有的人刚刚毕业,演出经验少一些;有的人是演过十几年戏的演员。我其实想用专业演员来做这个戏。
《大师和玛格丽特》剧照。图/摄影师 塔苏
新周刊:昨天看大师跟玛格丽特这两位演员的表演状态,感觉很返璞归真,看不太出来专业演员和素人演员的边界。
李建军:一方面,我的作品包含我的一个审美选择,我不喜欢很夸张的表演,我认为好的表演是恰如其分的表演,这样的选择会形成一种风格。其实选择演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戏的一种表演风格。
另一方面,表演的各种方法、各种风格的美学光谱是很大的,我不觉得演戏一定要演得像我小时候看的话剧那样浓墨重彩。
新周刊:您曾说过,使用素人演员,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对现有的美学关系、美学霸权发出质疑。近两年的创作用的都是专业演员,这是因为如今再强调“素人叙事”,也再难达到十年前那样“解放普通人”的艺术效果。由此发散,这会不会是您这一代导演在创作上的共同难题,以前的先锋意识和实验表达,在现代化社交媒体等外部环境的摧枯拉朽的攻势之下,瞬间丧失了力量,或者说在新的话语体系下失效了。那接下来还能挑战什么,还有什么表达是重要的、必要的,是值得关注的,是能贴近生活的?
李建军:现场演出是媒体对人的表达权利的一种解放。在素人的表达权利不再像我2013年做《美好的一天》时那么有张力的时候,选择回到舞台上进行表达,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转变。那就是我作为一个戏剧导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美好的一天》剧照。图/摄影师 李晏
我做素人的戏的时候,不在剧场里做,也是在做一种表达;如果回到剧场里,把这些美学的东西抛开之后,可能至关重要的是你讲什么问题、你的选题是什么?那个环境消失、改变了,(但是)现场依然在我们生活中存在着,你在现场所能够做的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就是你在舞台上讲什么故事、讲什么话题,你要对观众说什么。
如果要说变化的话,我觉得我对于美学叛逆的企图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首先是我有什么真正的痛点,很真诚地对观众讲出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其次才是我怎么去讲,有这样的一种偏移。
新周刊:你所说的痛点会随着时间被掩盖、变平淡,还是会随着您的创造变得越来越强烈?
李建军:它是一个生长的过程。比如说在做《狂人日记》的时候,它可能像是一种摇滚乐式的愤怒,像一个年轻人的表达。在今天这个小说里,面对这样一个载体,什么是救赎、勇敢、爱?那些在年轻的时候觉得离我很远的话题,好像离我更近了、更急迫了。我觉得即使今天的年轻人不会面对(这些问题),他们总有一天会面对的。这个生长就决定了我表达方式的一种偏移。
《狂人日记》剧照。图/新青年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