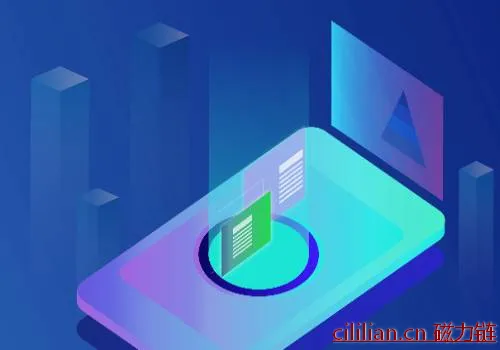小时候在老家,每年的农历三月,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田野里长出许多绿油油的荠菜时,姥姥总会为我采挖一些回来做菜吃。至今,那种清香还回味无穷。
(资料图)那时,自己还是个五六岁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跟着姥姥到坡里挖荠菜。姥姥提个手编的柳条小筐,拿一把小铲走在小路上,我则颠颠地跟在后面乱跑。
到了田野里,荠菜长什么样,我也不认识,姥姥会指着地上长出来的荠菜教给我怎样辨认。荠菜叶片细长,两边呈齿状,开出的小花像白色点子,通常长在阳面的荠菜又肥又壮,阴面的荠菜长得瘦长,颜色也更绿一些。有的荠菜的叶面上好像还蒙着一层灰白的茸毛,它那特有的沁人心脾的清甜味儿,让人格外喜欢。
姥姥说,麦地里的荠菜最好,又壮又嫩。然后很认真地示范给我,怎样用小铲子把它挖出来。但我认识了荠菜的模样后,只要看到是荠菜,就不管肥瘦嫩枯,不加选择地统统挖出来,正所谓“挖到篮子里的就是菜”。荠菜的生命力很强,长势也很旺,若是能遇到一场春雨,荠菜会长得更加旺盛。那个年代,清晨和傍晚,挖荠菜的人会很多,大家挖荠菜大都是为了贴补口粮的不足,很少是为了品尝荠菜的鲜美味道的。荠菜的生长期也很短,过了农历三月它就很快开出星星点点的小白花,也就老的不能食用了。
八九岁以后,每当到了碧绿的荠菜在坡里等待着我们的时候,我便不再和姥姥一块去了。而是放学后或星期天,只要谁说一声挖荠菜,我们三五个同龄的小姑娘,立刻就跑回家带上小筐、小铲子,像出笼的小鸟回归自然一样,叽叽喳喳向着广袤的田野奔去。麦田里、田埂上,清风在耳畔浅吟,那些嫩生生的荠菜,在微风中挥动着绿色的小手,好像在招呼着我们,欢迎着我们。当我们手提一篮满满的荠菜回家时,那种天真快乐,那种满足和成就感,现在回想起来简直还是一种满满的享受。
通常我把荠菜挖回来后,姥姥就叫我拿个小板凳,给我一把剪刀,让我在院子里把荠菜的根一棵一棵地剪掉。那时我会很认真的,像接受了什么重大任务一样,嘴里哼着现在想不起歌词的儿歌,坐在板凳上一棵一棵地择着荠菜,我家的小黄狗也会摇头摆尾的在我身边蹭来蹭去的陪着。看到嫩绿的荠菜,院子里的那两只大白鹅,也会不失时机的昂首挺胸,哦哦哦地叫着跑上来抢走几棵尽享饱腹之乐。
荠菜择完后,姥姥就把它们放进清水中浸洗干净,锅里放上油炒一炒,然后撒上豆面,加上少量的水,在锅里炖煮10几分钟后,掀开锅盖放上盐。就这样,鲜美的荠豆菜就做好了。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白绿相间、味美鲜嫩的荠豆菜,吃了还想吃。荠菜在生活困难的年代给我们增加了生命的动力,为我们度过困难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它也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多少年过去了,荠菜还是那荠菜,但荠菜的身价已不是往日的身价,已从分文不值的野生植物,成为市场上抢手的小商品。从穷人家的口粮补贴物,成为现代人餐桌上的美味。感慨万千之余,我对荠菜至今还是深怀感激之情。如今,荠菜也成为农村人增加收入的一种补充,我们也不用费时费力地到田间地头去挖了。每年农历三月份荠菜上市的时候,大清早,小区的街道两旁或集市上就会摆满鲜绿的荠菜。每次我都忍不住要去买来一些,用荠菜配上肉包水饺,或是做豆腐海米素水饺,或是用开水把荠菜汆了,加上麻汁蒜泥拌着吃。也会把汆好了的荠菜储一些在冰柜里冬天吃。
在有荠菜的日子里,自然会想起那悠悠的童年趣事,思恋儿时的伙伴,怀念跟着姥姥挖荠菜时,跳着、跑着、唱着的情景,寻回一些失落了多年的根系上沾着潮湿泥土味的一簇簇荠菜情。每每那时,山村和煦的阳光、绿色的田野,姥姥家的小黄狗、大白鹅……还是那样的亲近而挂肚牵肠。
。
作者简介:李玉华,女,1956年11月出生,博山区图书馆退休馆员。喜欢读书,热爱文字,乐于在生活的烟熏火燎中,感悟人生,盘点过往,蒸腾情愫,追寻心迹,感恩所遇。曾出版文集《我的婆婆我的娘》。
壹点号 文学博山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