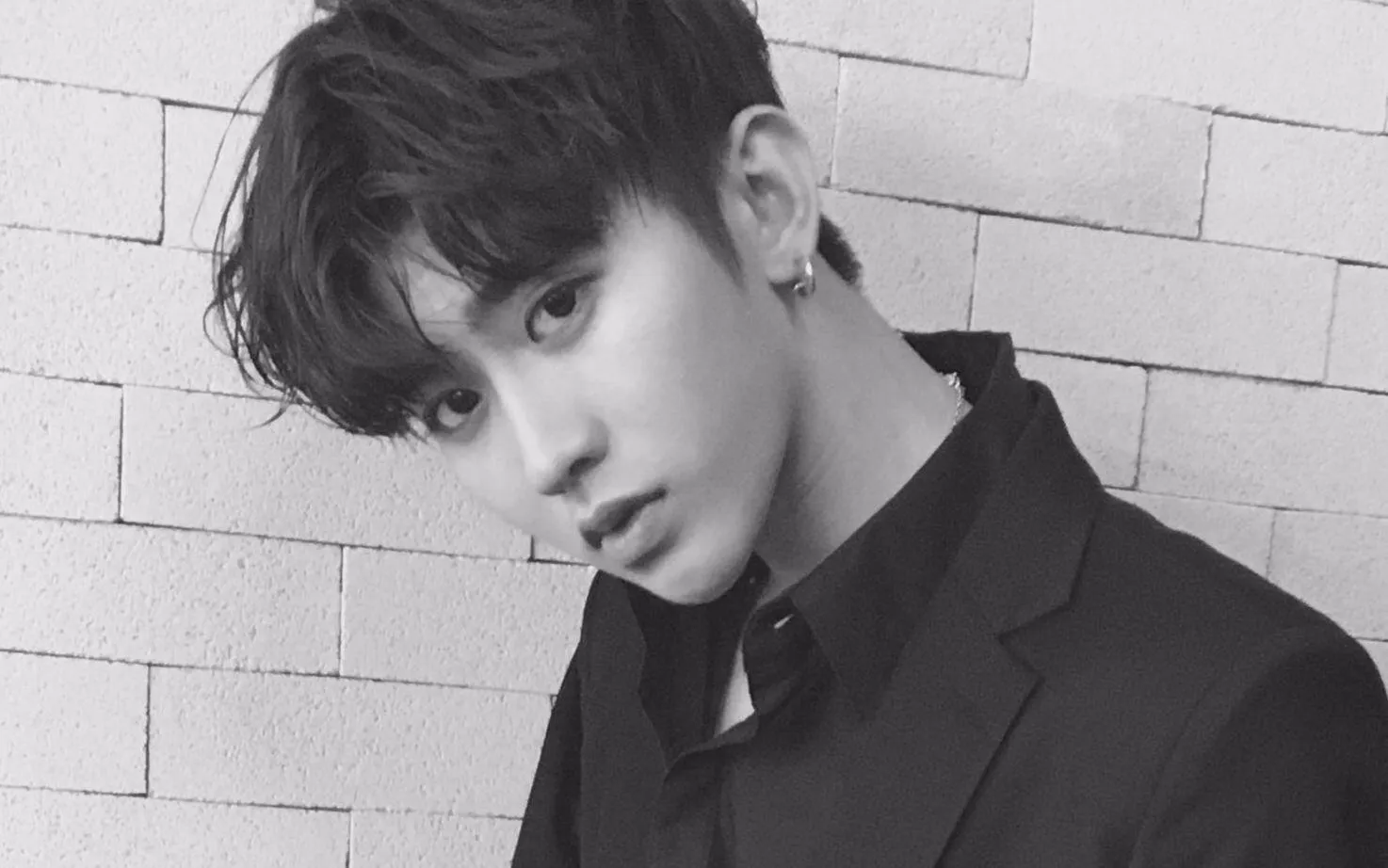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
(资料图片)◎李勤余
《保你平安》还是大鹏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主角必然是落魄不得志的小人物,叙事必然是对当下各类流行梗的融合(这回是网络暴力、性别议题和后真相),主题必然是倡导“做个好人”(毛不易演唱的主题曲《祝你平安》几乎把传统价值观直接糊到了观众脸上)。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从《煎饼侠》《缝纫机乐队》到《吉祥如意》再到如今的《保你平安》,大鹏逐渐去除了早期喜剧中的过火和癫狂,在技法和套路方面的日趋成熟是肉眼可见的,但他对“嵌套结构”的情有独钟却从未改变。
从框架文本到嵌入文本
在大鹏的电影里,观众总是先接触到框架文本,随后才慢慢接触到嵌入文本。
框架文本往往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窘境,然后一出“人格破产”的好戏就此上演。《煎饼侠》里,人气偶像大鹏遭遇意外事件,爱情和事业双双跌入谷底;《缝纫机乐队》里,经纪人程宫似乎完全丧失了对音乐、对摇滚的兴趣,一出场就是个胸无大志且唯利是图的市侩角色。
再看两部虽不是大鹏导演但由其主演,且带有浓重“大鹏色彩”的电影。《受益人》里,一事无成、穷困潦倒的吴海为了给罹患哮喘的6岁儿子治病,动起了“杀妻骗保”的歪脑筋;《大赢家》里的严谨是个十足的怪咖,凡事认真到了刻板的地步,不光得罪行长,还连累同事奖金泡汤,人际关系一团糟。
如今《保你平安》里的魏平安虽号称“集安断尾虎”,实质上又是一个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失意中年男子——被前妻嫌弃,被女儿蔑视,连自己那辆老爷车的后备箱都和他作对。
框架文本的铺垫到位之后,就是大鹏的拿手绝活——用“戏中戏”的方式展示嵌入文本,比如小人物的理想主义,比如主人公的真善美。
“煎饼侠”的电影梦看似疯狂、荒诞,却让大鹏领悟“成为自己的英雄”最重要;程宫在乐队成员的感染下,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利益,选择重拾自己的摇滚梦;吴海被妻子的真情打动,借一次洗心革面的机会获得了对方的宽恕与谅解;严谨则通过银行演习让所有同事了解到“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珍贵。同样,《保你平安》最终渲染和突出了看似不靠谱的魏平安身上所承载着的“主持公道”的侠义精神和“好人有好报”的道德伦理。
可是问题来了:既然主题如此清楚,大鹏何必总要在自己的电影里大费周章地玩“嵌套结构”和“戏中戏”,就不能直抒胸臆吗?
答案很简单,如果说大鹏电影主人公出场时总是自带权利和身份的被挤压感和被削弱感,那么“嵌套结构”给他们带来的就是一种心灵上的保护。小人物要“逆袭”,必然离不开行动和抗争。可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困境终究是小人物力不能及的,于是,大鹏反复用“嵌入文本”安慰身处“框架文本”的小人物——我们改变不了外在的世界,但没有关系,我们的内在品质本身就是可贵的。正如魏平安在电影中得到的最高评价——“你是一个好人。”
“嵌套结构”里的裂痕
《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为推迟自己的死期而给国王讲故事,但作为嵌入文本的故事再美妙,讲完之后,他终究还要面对回到框架文本的现实。这也意味着,“嵌套结构”在连接处出现裂痕,或许是无可避免的。
《煎饼侠》里的大鹏在有意无意间隐去了一场重头戏,这场戏本来应该交代他想要拍的超级英雄电影到底哪来的资金和人脉,他自己的丑闻又是如何“洗白”的。从这个致命的问题开始,大鹏电影里关于逆袭的想象性似乎就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大鹏给出的应对方案是,在框架文本之外引入一个从天而降的“救世主”。《大赢家》中严谨在演习中荒诞至极的行动之所以能进行到底,全靠警察局长的支持;《受益者》里的吴海能假戏真做,收获美满的人生结局,全靠善良到难以置信的妻子;《缝纫机乐队》中,让当地政府收回开发土地经济计划的,竟然是一场摇滚音乐会。
《保你平安》依然沿用这一设定。魏平安为澄清网络谣言“千里追凶”,但最关键的一步其实是阴错阳差跟随而来的公安干警,否则他捉到了造谣者也很难让其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魏平安的女儿勇敢为同学申冤的行为和魏平安的壮举形成互文,但这同样离不开“学校”和“老师”的支持——如果学校方面选择息事宁人,又会怎么样呢?
这体现出的是创作者既不敢让电影违反规矩(小人物的愿望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又想要讨好市场和公众(小人物也不能“倒霉”到底)的纠结心态。与其说大鹏总是想在电影中做到左右逢源,不如说其很难突破自相矛盾的困境。由此也可以解释,大鹏电影中的逻辑漏洞为何总是特别明显——主题先行,类型既定,随后罗织“嵌套结构”的创作方式终究和真实的生活间存在着一定的隔膜。
大鹏的反身性思考
大鹏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在同样以“嵌套结构”构筑起来的《吉祥如意》里,大鹏借他者的视角审视自我、认识自我,实现了一种反身性的批判思考。
影片中的核心矛盾是多年未回家的女儿王庆丽该如何解决父亲王吉祥的抚养问题。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是,片中扮演王庆丽的演员刘陆问真正的王庆丽,“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十年不回来”,于是王庆丽由刘陆这面他者之镜,直观地认识到了自我处境。她的沉默不语是最直观的反身性思考,而这也是《吉祥如意》最可贵的地方——对复杂、暧昧的传统家庭伦理,大鹏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只留下一声叹息。
令人欣喜的是,这种反身性思考也在《保你平安》得以延续。魏平安没有像其他大鹏电影主人公一样实现“逆袭”,说明小人物做好事未必一定要成为大英雄,可能只是为了“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做你认为正确的事);马丽饰演的冯总也不再是大鹏电影里为富必不仁的刻板形象,一句“大家说我是毒枭”说明了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可能是每一个人;魏平安最后抓住了造谣者,但互联网的传播机制并没有发生改变,他的粉丝“一枝花”同样在利用魏平安的故事创造流量。
魏平安的手机在电影里不停变换着视角:微信的聊天界面、直播界面、视频跟拍……“观看”不仅成了电影“戏中戏”里的关键词,也说明人们的窥私欲不会因为魏平安创造出的一桩偶然事件而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终于,大鹏的“嵌套结构”不再是主题先行的产物,而是嵌入文本与框架文本融合、碰撞后的深刻感悟——既然身处互联网时代的我们都逃不脱被“观看”的命运,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用善意的目光去“观看”新闻、“观看”视频中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
当魏平安在江边凝视着绚烂的烟花,耳边响起《祝你平安》熟悉的旋律时,观众确实可以感受到不同于以往的真挚力量。就此而言,《保你平安》或许还不完美,但大鹏确实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