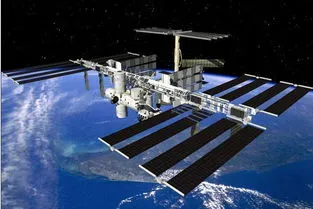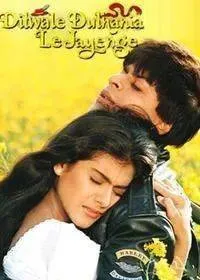11月25日到12月4日,第九届乌镇戏剧节顺利举办。今年特邀剧目单元和青年竞演单元汇集了众多作品,小镇对话、嘉年华活动不可谓不丰富。这正应了今年戏剧节的口号“丰俭由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办方和创作者竭力提供“丰”,观众则各自“由人”、各取所需,共同营造一种乐观开放的艺术氛围。不过,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今年的乌镇相较往年多少有些冷清,几场雨雪更把气温直接拉到了冰点。雪花落在西市河上,腾起绵绵水雾,给整个戏剧节带来了别样的神秘和迷蒙。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细看之下今年戏剧节作品水平参差,让人情绪跌宕、五味杂陈。先说惊喜。今年最大的惊喜是青年竞演单元,其中又以最佳戏剧奖作品《月亮光光》为最。该戏将电视节目、僵尸、驱邪等多种元素结合起来,粤语对话把人带入了故意做旧的、现在看来略显粗糙的老港片怀旧氛围之中,对银幕、字幕的巧妙使用不仅连接了虚构的人界和灵界,也连接起过去和当下。与之类似,作品《点》也有着不错的想法,虽然以虫喻人多少有点用力过猛,但很多这样的青年戏剧都在向我们表明,现实生活是戏剧创作的沃土,想象力则是青年戏剧的无上法宝。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戏剧与全世界戏剧经历的危机一致:疫情客观上阻断了想法和人的流通,而戏剧恰巧就是一门极度讲求交流的艺术。一些戏都很明显地在沟通方面面临巨大问题,一些戏的想法尚可,但在具体执行上没能精细加工打磨,虚假的交流和反应随处可见,令人很难直视。
而从主观上看,国内很多创作令人遗憾地走上了一条内循环之路,呈现出闭门造车的趋向:无论是美学、手法还是表达上,都惊人地和时代、和世界脱节。举例而言,话剧《红高粱家族》以一种极其古老的、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姿态注视着高密的男男女女;《樱桃园》极其大胆地完全肢解了契诃夫的文本,可惜导演没有足够的替代力量,只是简单地征用了一个现代舞空壳,很难称得上是一次合格的尝试。从这两个戏来看,如何演好“大戏”、如何诠释经典文本,始终是创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为观众,笔者深切地期待戏剧有能力表述现实、表述新的时代议题。然而遗憾的是,想要看到这样的作品并不容易。
在今年乌镇的作品之中,有一部格外出众,那便是新青年剧团导演李建军执导的《大师和玛格丽特》。该戏改编自苏联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讲述了“大师”和他的爱人“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其间还穿插了撒旦大闹莫斯科、伊万误入疯人院等多条处在不同时空的线索。几组情节透过演员、影像和空间组织起来,历史与现实、演员与角色、台前与幕后诸种界线逐渐模糊,却也绝不散乱。李建军和编剧对原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虽则个别处理值得商榷,但其切入现实的力度亦不容忽视。
诚如李建军所说,“什么对于我们是真问题?不是那个经典的遗产,而是我们生活的痛点。”戏剧需要面对的是活生生的观众,而不是死气沉沉的教条。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获得希望和力量,才能从令人窒息的红色高粱地或者蓝色大海里浮游而出,走向更宽广的、五彩斑斓的世界。
乌镇戏剧节期间,北青艺评对导演李建军进行了专访。
布尔加科夫强大的文字是改编者的一道坎
北青艺评:首先恭喜《大师和玛格丽特》首演成功,这个戏让人感到非常振奋。
李建军:这首先得感谢乌镇戏剧节。我参加乌镇戏剧节很多次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基本不会对我有太多限定,这非常难得。其次小说的基础也非常好,《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一部批判性很强的作品,所以观众看这个戏会有很强烈的感受,至少一些观众给我这样的反馈。
北青艺评:您对这部文学作品是怎样的看法?
李建军:最开始是上大学的时候。这本书在1993年或者1994年有了中文译本,当时是畅销书,但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如果有印象的话可能是它接近《西游记》——小说中有些很经典的桥段,比如撒旦大闹莫斯科、玛格丽特在天空中飞。这些是每一个读者都会印象特别深刻的,我的印象其实就是这些。
2013年元旦,我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看过一个改编版本,但完全没有印象,说明那个版本很糟糕。这次我也研究了很多根据《大师和玛格丽特》改编的舞台剧版本,感觉没有一个舞台的想象力能够和文学的想象力媲美。这是做这个戏很难的地方,因为布尔加科夫文字的想象力实在太饱满了,对改编者来说,其实是需要迈过的一道坎。
北青艺评:后来是什么时候再看小说,怎么想到要转化成舞台剧?
李建军:重新翻出来读就是疫情这两年。以前我觉得这是完全无法被舞台化的文学,一方面是文学性太强大了,另一方面是宗教背景非常强,本丢·彼拉多在小说中有非常强的存在感,这可能是中国观众完全无法跨越的。但这些年我在生活中真正开始触碰、思考一些很重要的命题,比如关于爱的主题,我们怎么能够活下去,要如何活着,人的生命力应该是什么……对这些有了很深的感触,而这部小说恰好也涉及这些。做了这么多年舞台剧,到了这个年龄,突然对勇敢与怯懦、死亡与恐惧、爱在生命里意味着什么,有了一些感受,所以觉得改编成为一种可能。
压力很大,因为把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都拿掉了
北青艺评:您觉得改编前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为什么这样改编?
李建军:改编和小说的区别挺大的。首先就是原书前300页基本都是撒旦大闹莫斯科,现在我们把这条线索弱化,突出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改动。还有就是结尾。原书的结尾是宗教式的:现实中苦难没有办法也解脱不了,所以玛格丽特复仇之后,上帝派撒旦给他们喝下毒药,把他们带到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的世界,两个人去了彼岸。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让二人回到了现实中。
北青艺评:关于戏中的新结尾,您在这个戏进行到大概三分之二处就已经预告了,有什么样的考虑,为什么一定要让二位主人公回到现实?
李建军:布尔加科夫本人是上世纪40年代去世的,当时《大师和玛格丽特》还没有发表。所以从小说家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救赎的结尾在我看来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结局。其实我和编剧曾经有过很多其他的设想,因为中国的文化和现实,与布尔加科夫经历的那段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最终都会觉得当中国人投射自身的经历和体验的时候,那样一个结尾毕竟还是太虚了。所以最终还是确定两个人的结局应该是回到小屋、回到现实,面对残酷的世界,勇敢地前进。戏剧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是给此时此刻的观众看的,对象感非常强,我做戏的立场是这样的。不过我和编剧对这个结局应该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其实一直比较模糊,直到很晚才确定剧情要这样走下去。
北青艺评:您和两位编剧的合作方式是怎样的?
李建军:我们的做法其实有点像电影导演和编剧。我和编剧马璇从3月份就开始聊,有一个改编的方向,每一段戏的铺排就像推演一样,边聊边写,边写边进入排练的过程。也有很多不顺的时候,到最后觉得进度太慢了,要完不成了,好像掉到一个漩涡里了,所以需要另一个人来帮助我们,到今年11月的时候编剧胡璇艺加入。
北青艺评:这个“漩涡”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李建军:一方面是本质性的:做舞台剧和电影不太一样的地方可能在于,舞台剧直到演出之前都可能还会有颠覆性的改变;而电影的工业化制作流程不允许这样的颠覆,所以我认为舞台剧无时无刻不在一种漩涡里。另一方面,“从当代看《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样一个构思其实很早就定下了,但要在这么庞杂的故事中取舍,确实大费周折。小说提出的勇敢、救赎、爱等很宏大的主题,一直在你旁边,只是创作的时候你可能看不见。理想之国又是什么?聊的时候是对的,写出来又觉得很虚妄。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主题上,离小说的文学性远一些。小说和改编是一种关系,不能完全躲着,也不能被小说淹没掉。我想如果勇敢地站在这个角度思考,会选择现在这样一个结尾。但当局者迷,这是创作者的局限。
北青艺评:这个戏上手之后,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李建军:我觉得每个部分都很困难,但如果说最困难,那可能还是小说和改编这组关系。我压力之所以很大,是因为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都给拿掉了(笑),比如魔鬼有四个随从,他们的戏很精彩,全部去掉了,这对很多创作者而言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我看了很多版本,撒旦都是绝对的主角。怎么面对这样一个巨人一样的文本啊!会有一种要扯着自己的头发跃过去的感觉。我和马璇有过自我怀疑,这种情绪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在。但如果想逃离自我怀疑,只有诚实地面对自己才可以。什么对于我们是真问题?不是那个经典遗产,而是我们生活的痛点。所以最后如此直接、很决绝地站在一个立场上表达,也是自我挣扎的结果。
制造一种时空的重复感讲故事其实是在讲今天
北青艺评:这个戏使用了大量影像,怎么决定使用,有什么样的构思?
李建军:影像的使用主要还是跟这个戏最根本的构思有关。它涉及到过去和今天的对照,涉及到一种“穿越”。在戏里,撒旦以现代人的面目现身;玛格丽特从小说穿越到现在;演员和角色之间界线模糊;所有这些都是有对照的用意的,这种关系必须让观众看到。有了这个构思,影像自然就被纳入进来了,比如要在化妆间看到表演,就要靠实时的影像;比如伪纪录片就是把现代的街景用胶片的颗粒变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感觉;比如伊万进精神病院的那个唱段,用的是演员的照片,但是黑白处理配上文字之后,看上去变成了那个时代的角色。这些影像都是为了创造对照关系。
北青艺评:还有一些爆炸的慢镜头,那个段落似乎和电影有很直接的关系。
李建军:那一段真的是去棚里爆炸的,但当天实在太晚了,爆炸会被投诉,所以不敢用大量的炸药。最后舞台上用了一些镜头是电影《扎布里斯基角》的片段。这个电影是我大学时期看的,印象非常深,创作的时候那个画面一下子就出现在脑子里了。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这个戏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没完成,这是我十来年心里最没底的一个戏:首演当天,观众进场前20多分钟我们刚完成了彩排合成,还在改戏,观众能在外面听到试麦的声音。整个过程都是很狼狈很仓促的。
北青艺评:提到电影,摄影机的调度也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李建军:都是在排练过程里形成的,跟演员在舞台上的调度是一样的。比如第一场戏讲爱情的时候,摄影机空间要小一些,让观众联想到这是在小屋里;演员从角色里跳出,景别就要大一些,让观众感到这是在阐释角色。我自己对电影非常感兴趣,所以舞台上用这些还是出于某种乐趣。传统舞台在空间上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我会用影像。影像进入现场之后,空间就产生了很多种新玩法。
北青艺评:舞台空间比上一个作品《世界旦夕之间》难度翻了好几番。
李建军:一些空间要通过表演来实现,比如角色在讲故事,伊万那一段就可能要戴上面具完成空间的转换,这是舞台剧的传统。化妆间和舞台,是靠不同的物质分割开来的。化妆间本身也可以再做分割——它既是现实的化妆间本身,又可以变成本丢的宫殿,所以本丢出现的时候要用黑白影像,和现在有一点时间距离的感觉。
总的来说,主题是最根本的,空间必须依照这个原则设定,没有这个思路的时候就会瞎想。“穿越”是结构空间的一个基本思路,要有区分有连接。这个剧很多时候是用一种时间穿过另一种时间来组织空间,观众的时间和空间感会模糊,从而产生一种历史的重复感。最终我们要让观众意识到,讲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讲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