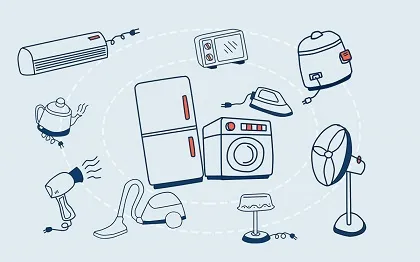独居者是否可以在人生晚年选择在家临终?这是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教授在她的两本新书中探讨的核心问题,通过思考、阅读、调查,与相关研究者、医护从业者讨论交流,她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可以的,完全没问题。独居的障碍虽然很多,但完全可以跨越。”作为一位自身步入老年的研究者,她在不断变迁的社会文化、政策制度中,思考着老年生活、临终方式的可能性。
(资料图)上野千鹤子因其女性主义理论与著作而为中国的读者熟知,实际上老龄化社会也是她长期关注的一个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译林出版社)、《一个人可以在家告别人生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就是其中新近译介为中文的两本。前者是她结合自身经验、社会调查及与相关专家的讨论,阐述自己对独自居家临终的观点理念,后者则是她与有丰富医疗工作经验的小笠原文雄医生的对话,更进一步探讨在日本医疗照护体系之下居家临终的可行性。
这不仅仅是基于个人经验而产生的困惑,在当前的人口结构背景之下,向社会抛出这个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达到28.8%,被称为“超老龄化社会”,这也意味着随后即将步入“大规模去世的社会”,如何终老成为一项亟待回答的问题。尽管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护理体系、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但两国共享着相似的老龄化趋势与家庭文化,因此上野教授抛出的问题、提出的观点仍然可以对我们思考当下中国的养老与临终问题有所启发。
何为幸福晚年?
日本有着大家庭文化,对于幸福晚年的认知是与家人共同生活、在儿孙的环绕下辞世,因此舆论普遍对独自生活的老人持同情态度,关于“孤独死”的忧虑也常见诸媒体讨论之中。但上野千鹤子认为,老年人与子女分户,独自居住,对于他们来说也可能是一种更幸福的生活方式。她认为,幸福的晚年生活包含三个要素:第一,在自己熟悉的家中生活;第二,拥有好的人际关系,这比有钱更加重要;第三,过着不迁就他人但是同时又自律的生活。
人们的养老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普遍认为“和子女同住是幸福的”,而现在很多人更接受“不住在一起才是明智的”,过去将独居视为“悲惨”,而现在很多人的理念是“独居才是快活的”。所谓“孤独终老”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独自一人生活,而是经济贫困、缺少社会联系,应该将被迫独居和主动选择独居分开讨论。特别是对于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来说,独自生活可能是他们更偏好的生活方式。
总而言之,“单身老人”的形象并不一定是悲惨的,独居老人不断增多也将成为不可回避的趋势,不如去了解老年人的实际愿望,积极思考如何创造更适合独居养老的社会支持网络。
居家临终等于“孤独死”吗?
“孤独死”是近来日本媒体热议的一项社会问题,对此,上野老师发问:“一个老人独自生活,直到最后去世,有什么错吗?”她综合各类报道与统计中对孤独死问题的讨论,梳理了定义孤独死的要素,一一予以审视:首先,意味着独居者在家中过世。但是由于各个年龄段单身户的比例增加,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必然有增强的趋势;其次,死后超过一定时间被发现。对于时间的长短各地规定不一,但是发生这样的情形,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时间长短,而是死者在生前就过着孤立无援的生活。居家临终并不等于孤独,也不等于失去与社会的联系,因此关键不是如何“防止孤独死”,而是“防止生活孤立无援”,应该讨论的是如何为独居老人建立社交与照料网络。
接下来,上野着重讨论了“孤独死”的另一个特征——去世时无见证人在场。但是,老年人是否真的都希望在家人的注视下告别人世呢?上野与小笠原医生就此进行了讨论,患者、家属、医护往往都秉持着“临终看护要由家人亲自来执行”的理念,但在实践中可能会面临复杂的状况。
有时,临终家人陪伴未必是老年人的愿望,而是家人的固执。小笠原医生讲述了自己遇到的一个案例:医护人员秉承着要让家人见到患者最后一面的理念而采取了维持生命的治疗手段,家人赶到医院后患者又生存了三周,但最后还是在家人不在时在痛苦中故去了。这让小笠原医生开始思考是否应该执着于老人临终时家人必须在其左右的理念,尤其是为实现这一点,需要对患者施以带来痛苦的治疗方式,且并不一定符合患者本人的意愿。他认为,“比起家人,比起常识,要毫不犹豫地优先考虑患者本人的希望与利益”。
他经历的另一个案例中,患者如愿在家中安详过世,但他的妻子因未能在场而陷入悔恨情绪,和家人产生冲突,自己的身体也受到影响。在小笠原医生的开导下,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是按照自己觉得幸福的方式离去的,身体状况随之好转起来,和家人的关系也有所缓和。他们认为,离世时有家人陪伴左右是好的愿望,但是常常无法实现,与其执着于临终时是否有家人陪伴,更应该在活着时维持好的关系,表达感激,不留遗憾。
相较于“孤独死”这个可能会引起恐惧感的词语,上野教授更愿意用“在家独自临终”这个含义清晰、更为中性的说法,并呼吁应该将焦点从对“孤独死”的关注转向对孤立无援的晚年生活的关注。
认知障碍症的难题
老年人的愿望是自己在熟悉的家中生活,但分开居住的家人出于担心,希望老人进入养老院、疗养所,那么,是应该尊重本人意愿?还是将安全的考虑放在首位?这个两难在老年人患上认知障碍症的情形下更为难解。
认知障碍症患者失去了自主决定的能力,往往在家人的安排下入住养老院、护理机构,虽然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但是由于机构人手有限,老年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出门活动,甚至有的养老机构通过药物抑制行为,这些措施都使得他们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但另一方面,认知障碍者独居虽满足了本人的愿望,精神状态可能会更好,随之而来的却是存在重重风险——缺少社会交往加重症状、不停走动导致走失或发生交通事故、意外摔倒造成骨折、忘记关火引发火灾等。
有数据预测称,到2025年,日本的认知障碍症患者数量将达到700万人,每4到5位老人当中就会有1位患有认知障碍。上野认为,与其对认知障碍症恐惧,把所有努力投入在预防上,更应该去努力建设一个可以“患上认知障碍症也能放心”的社会。衰老就像是从健康状态逐渐步入“后天残疾”,那么就像对于残疾人融入社会的理念一样,我们努力建设一个无论身体是否有残障都可以舒适生活的社会环境,不仅是“即使患上认知障碍症也不要紧”,还要实现“患上认知障碍症后依然美好”的社会,更进一步迈向“对认知障碍症胸有成竹”的社会。上野老师俏皮地写道:“这最好在我患上认知障碍症之前就能实现。”
构建居家支持体系
两本书中还讨论了让居家临终成为可能的一项重要制度,即日本的护理保险,该制度从2000年正式实施起已经有20多年,建立起了护理服务的市场,培养了相关的专业人才,积累了许多经验。护理保险采用个人缴纳保险费和税收支出结合的形式,护理服务由专门的服务商提供,其中一项便是居家护理服务,专业人员可以上门提供身体护理和家务援助。老年人需要进行护理等级认定,按照其日常生活能力认定为相应的1至5等级,确定能够使用的护理保险的上限,超过的部分由个人负担。在护理社会化的实践之下,居家护理服务从一开始面临着对陌生人到家中服务的质疑和抵触,需要公务员挨家挨户访问、挖掘用户,到很快就需要修订政策来抑制使用,“护理不仅仅是家庭责任”的观念得到了更广泛的接纳。
上野认为护理保险制度也带来了护理工作的有偿化与专业化,原先在家中由女性承担的“三无劳动”(无人感恩、无人认可、无等价报酬)变得可见,让人们意识到这是需要支付相应报酬的辛苦付出。护理工作者需要经历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能从业,这也打破了将家务与护理视为女性“天然胜任”的刻板印象,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于照护工作低技能的偏见,提高了护理从业者的薪资和社会地位。
当然,上野也分析了日本护理保险存在的种种局限和问题,比如缺少对贫困群体的帮助、制度的改革为用户使用施加了更多限制等。但她认为,这样一项制度是护理社会化的重要一步,在家庭护理能力衰落的背景之下,对于老年人及其家庭是非常有益的政策,尤其是切实地帮助到了独居的老人。因此,她发出“不许护理保险开倒车”的倡议。
宏观的政策制度之外,小笠原医生指出,来自专业的居家临终关怀姑息治疗团队提供的支持与服务,对于实现老年人居家临终的愿望非常重要,这也是他致力于实践与推广的领域。这个团队里包含了牙医、药剂师、护士、专业护理人员、护工等多种职业,他们根据患者需要,共同合作进行居家医疗。服务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以预防和控制病情为目标定期到家中访诊,其次是进行姑息治疗,施以减轻痛苦的舒缓治疗以及提供心理支持的疗护服务,第三是纳入生命与临终关怀的哲学理念。
不只是专业人士,老年人在社区当中也能够得到来自友邻的关怀和帮助,朋友、附近的居民、志愿者、邮递员都可以发挥看护的作用。比如有牛奶配送员发现信箱堆积了许多报纸,及时报警,从而避免了一起孤独死事件的发生。有了专业护理服务团队、社会支持网络,独居者就并不是“孤独而死”。
“衰老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死亡的概率是100%。”超老龄化社会意味着“缓慢地死亡”,上野老师将迎接死亡比作慢慢地走一段下坡路,在当前的社会经济与医疗水平下,大多数人是渐渐衰老,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依赖他人护理。
从两本书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起“孤独死”的负面刻板印象,更应该了解、尊重老年人自己的意愿。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很多努力,我们可以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思考关于养老与临终的理念以及如何构建相应的制度与支持体系。就像上野千鹤子所呼吁的那样:建设一个需要护理也能让人感到安心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