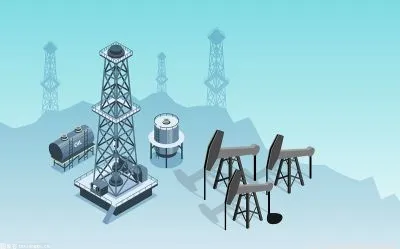(资料图)
对于国内城市形象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较早的应是赵园的《北京:城与人》。该书并不是展现关于北京的现代城市文学史,而是以确定北京在中国作家心目中的位置入手,事实上,是在为“文学中的北京”进行定位。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北京其实替代了乡土中国的国家与文化地位,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故乡。从这一角度看,北京也是一个想象中的城市。它既负载着真实的物理空间,同时又被文学建构成一种形象。由于创作时间较早,这一著作太过局限于文学形态,对于文学又较集中于京味风格的分析,使其相当程度上仍保留着城市文学形态研究的痕迹,未能获得某种讨论北京想象的广泛的可能性。
有意识地倡导以“记忆与想象”来对北京城市与北京文学进行研究的,是陈平原先生。2003年10月,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文系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联合主办“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研讨会,会议刊发以及后来收入论文集的研究论文来自各个学科,其中有数篇是关于北京与文学之关系的。其中,梅家玲的《女性小说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林海音与凌叔华的北京故事》、董玥的《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与贺桂梅的《时空流转现代:1980—19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大体也属于类似角度的研究。在谈及“作为研究方法的北京”时,陈平原也以“文学中的城市”为切入点。他说:“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谈论‘文学北京’乃是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口头传统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重现八百年古都风韵的设想。”“谈论中国的‘都市文学’,学界一般倾向于从20世纪说起,可假如着眼点是‘文学中的都市’,则又当别论。”而在谈到“文学中的北京”这一概念时,陈平原径直用“想象”一词去表述。在《“五方杂处”说北京》一文中,陈平原说:“略微了解北京作为都市研究的各个侧面,最后还是希望落实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上……因此,阅读历代关于北京的诗文,乃是借文学想象建构都市历史的一种有效手段。”
近代北京的人文景观具有明显的乡村特性,恐怕没有比“田园”一词更恰切的表述了。北京的建设格局有着极严谨的计划性,这与上海等租界城市因殖民者随意扩张而造成的混乱不同。元朝统治者修建大都,其宫苑结构非常散漫。明初皇宫被置于城之正中,其余地方空疏寥落,偌大京城其实只是预备日后的扩充,始终未曾布满,清王朝对北京的扩建基本上沿中央及南城进行。所以,一直到民国初年,城中依然满布着湖泊与园林,建筑并不密集。老北京人在天晴的时候,站在大街上便能望得见西山与北山。老舍曾说:“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
北京典型的建筑形式是四合院,比如皇城,可以说是北京最大的一个四合院。疏阔的庭院与园林自然相融一体,即使是市井细民也可借不花钱的“草花儿”尽享田园野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本是典型的乡村景观,而老舍将此句的“南”字改为“北”或“西”,竟也成为对北京城市景观的绝佳描绘,足以见出老北京的乡村形态。郁达夫当年就说过:北京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当代学者赵园亦认为:“田园式的城市是乡村的延伸,是乡村集镇的扩大。”应该说,北京的人文景观尚未取代自然景观,其乡土性可见一斑。
当然,在近代中国,任何传统型城市都无法抵御现代文明的侵蚀。北洋政府时期,外来文明借助列强的势力与上海的影响,给北京的城市形态增加了若干新质。市政与经济方面,有了西交民巷银行区、崇文门大街的洋行区、王府井的新式商业区,此外还有六国饭店等新式旅馆、娱乐设施与北大、清华、燕京等学府。这使我们无法再把近代北京与古代北京混为一谈。新与旧兼容一处,竟成为一种奇观。1930年代有人描述北京说:
从紫袍、黄褂的蒙古、西藏僧徒,蓝袍青褂的重辫老者,光头大肚的商人,蓝布罩袍的名士,中山服的军政服务人员,加上上海的种种,无不兼容并蓄。他们的思想,从忠君爱国一直到共产;他们的生活,从游牧民族一直到工厂的工人;他们的来历,从冰天雪地一直到炎天热海;他们的信仰,从拜佛一直到无神;他们的时代,从乾隆一直到一九三六,形形色色,比肩并存于一城之内,这是何等奇观!
北京已不纯然是一座传统城市了。应该说,对近代北京来说,外来文明的渗透,是一种文明进步的体现。它毕竟给北京带来了一个向现代城市发展的契机。在此影响下,北京城市形态开始发生嬗变,譬如大学,甚至可以成为新文化的中心以及引领力量。但是,由于北京缺少现代文明的基础——大工业与现代经济,其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并不顺利。这导致北京在城市形态进化中出现两种常见的情态:一是文化变异过程混杂而不是整体有序地进行,外来文明与传统底色杂糅而不是一种有机的结合;二是城市形态中的浅层结构首先发生变化,但由于现代经济的缺乏,深层结构尚难以改变。
但是,近现代北京城市的乡村文化形态,使许多作家在情感上得到一种亲近,赵园说:“在普遍的都市嫌恶中,把北京悄悄挑除在外。”老舍说:“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在众多作家心中,“家”的定义是由北京提供的。1930年代的文人一再谈到北京“住家为宜”,这个“住家”或许在心理学的含义更多一些。它意味着传统文化为现代的人们留下的一份宁静与安详,一种归属感。当北京失去首都地位,成为一座纯然的文化城的时候,这种感觉显得更为浓烈。在1920年代,我们很少看到眷念北京的文学,而1930年代,作家们对北京的向往与怀恋达到顶峰。1936年,上海的《宇宙风》杂志曾陆续推出“北平特辑”(共3辑),其中大部分文章以《北平一顾》为题结集出版。《立言画刊》和《歌谣周刊》也设立不少有关北京风情的专栏。有趣的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生活于上海,个中意味,颇值得仔细品尝。
北京的城市形态为作家提供了一种观察的实感,更是一种心理。这种心理来自生活经验,却不止于是生活实感,很大程度上,北京的形象也是一种作家心理的形象,并不完全来自城市形态,有的时候甚至来自“北京之外”。比如,老舍一生以北平为写作对象,但他那种对北平文化批判性的创作冲动,乃是由于客居英伦得到了西方文明的参照之后才萌发的。老舍步入创作生涯后直到从美国返国,很少再去北平,但依然在城市小说创作上达到了高峰。很明显,其城市意识的获得主要依赖于现代理性,而非北平的传统。如果一生蜗居北平,便没有老舍,也没有《骆驼祥子》与《四世同堂》。或许,也是以北京为部分作品表现对象的京派小说,之所以没有取得相当的成就,是否与京派文人当时没有走出北平或北方文化圈有关?文学中的北京形象,乃是熟悉北京但不一定是北京文化圈之内的作家所塑造的,正如同乡土文学乃是出身乡村却又寓居都市并获得现代性的作家所为一样。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