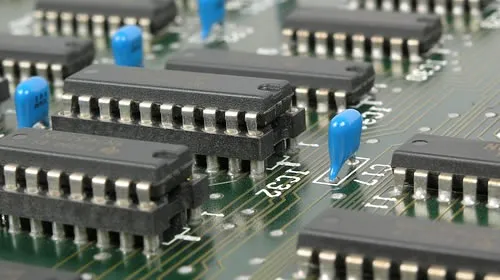在当下“短平快”的“读图”时代,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总是被选择性忽视,抑或那些经典的桥段湮没于记忆深处,仅仅泛起一阵阵不知从何而来的意识。不过,经典的世界名著应是常读常新,每一次重读都有新的体悟和新的理解。《读与被读——世界文学名著十一讲》即学人、作家、译者刘文飞教授在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文学课程的讲稿,邀读者重新体味世界文学名著,从西方文学源头之一《荷马史诗》到“新潮文学”源起之一的《洛丽塔》,收录了十一部文学名著的十一篇学术随笔。本书是寂静的,寂静到读者能够清楚地听到名著作者“被读”的声响,从而将我们引入文学研究的世界。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读与被读”虽是孤独,却如本书的封底所言,“读与被读”又是一种最渴望交流的举动,都充满对各种可能的奇遇之期待,都是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把握。孤独的文学读者与文学作者便是在这“读与被读”的联结中相互温存,我们亦通过“读与被读”对自我空间进行营造和突破,并与“信息茧房”进行持续的抗争。由此,“读与被读”也就成了世界上最为自由,至少是最富有自由精神的行为。
刘文飞教授是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学者,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等期刊编委。他的目光并不局限在俄语文学,而是精准地把握住世界文学深源的脉搏。对于本书的书名“读与被读”,刘文飞教授有一种寂静且独特的感知,一如他在本书序言的最后所述:“读与被读是一件与生俱来的事情,你吸入的第一口气就是读,你呼出的第一口气就是被读;读与被读是一桩相伴终身的事业,你吸入的最后一口气就是读,你呼出的最后一口气就是被读。”将阅读文学名著置于吐纳之间,一吸一呼,一吐一纳,便是文学名著的“读与被读”。
本书是讲稿集,亦是学术随笔集。学术随笔又称“软学术”,这一文体多为学术心得,亦有学术性较强的传记,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本书是学术文集新形式的探寻,亦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兼得。刘文飞教授曾在2015年接受《北京日报》的采访时提及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并重的观点:“在搞学术和做翻译的过程中,会有不少心得想和读者分享,这些心得成了‘多余的话’,放在哪里都不合适,所以我就写下来投给报刊,慢慢就变成了三条腿走路。”如今,刘文飞教授在本书中将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以学术随笔的方式合二为一,既回望古人做学问的基本方式,又呈现出现代主义的学术间性(“间性”即意味着对二元对立结构的扬弃,而是回归到互摄共融的状态,并关注各要素之间的影响及关联)创作观。
本书十一篇学术随笔,分别讲述荷马的两部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部小说、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川端康成的《雪国》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这些著作成书时间跨越近三千年,包括古希腊、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德国、法国、俄国、爱尔兰、日本和美国的经典著作,构成一幅世界文学的地图,亦如一部世界文学的简史论丛。
书中的每一篇学术随笔均以不同的切入点向读者讲述作品内容和作品的重点章节,并且一针见血地直接剖析出名著揭示的重要文学伦理观念。例如《哈姆雷特》向读者展现世界文学中双重性格的主人公、《巴黎圣母院》向读者引出宗教建筑与文学的相辅相成;《浮士德》向读者展示人类不屈不挠的求索、《雪国》向读者刻画出超脱且超然的死亡……
刘文飞教授将《荷马史诗》的悲悯置于开篇,向读者揭示“对人类苦难的感同身受,对任何一个具体人的具体不幸的深切同情,是每一位伟大作家展开创作的伦理前提”。文学始于对历史的述说,发展于对历史的超越,正如本书第一章结尾所言,“文学只不过是一种情感教育手段,意在发掘、展示并培养人类的高尚感情”。
倘若荷马的吐纳教诲我们文学与道德的内容联系,纳博科夫的吐纳则引发了我们对文学形式的深思。刘文飞教授将《洛丽塔》的多重解读置于本书的最后,则是现代文学读者对于传统文学评判的超越。美国报刊上对《洛丽塔》的不同评价,促成了小说的畅销,但对《洛丽塔》究竟是否为色情文学的争论烟消云散过后,读者们转而注重《洛丽塔》文体学的精妙,即形式的精妙。倘若对纳博科夫流亡美国之前的创作史了解些许,不难着眼于他从诗人摇身一变成为小说家的过程。作为诗人的纳博科夫是极富“间性”的,同时亦是极其注重文学形式的。以勃洛克、勃留索夫和吉皮乌斯等人代表的俄国象征主义,以及以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等人代表的阿克梅主义,分别从此岸和彼岸两个维度影响到纳博科夫。法国纯艺术派的精致,也通过上述两个流派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创作。可以说,纳博科夫始终走在将诗歌与小说两种文体拉近的路上,在《洛丽塔》中则表现为营造诗意以及细腻的心理感受。刘文飞教授由此将思考的问题置于文体的间性,此种间性是“记忆”与“技艺”的联系,也是诗与小说的联系。
有时,“怎么写”或比“写什么”更值得思考,我们亦能在本书中找寻到创作的密码。如《安娜·卡列尼娜》小说文本中的种种细节与读者之间泛起了接受美学的涟漪;再如《尤利西斯》的意识流,即小说中三个主角的思想和感受、想象和梦境、联想和幻觉共同构成《尤利西斯》叙事的主要对象,同样是对写作者的启示。
翻译的价值,尤其是文学翻译的价值在本书中亦不止一次地提及。刘文飞教授提及帕斯捷尔纳克创作《日瓦戈医生》,就受其翻译《哈姆雷特》的影响。本书多次援引名著的经典中译并标注译者,这些引文既是刘文飞教授的倾情推荐,还是对读者善意的提醒:译文的获取并非理所应当,而是译者辛勤劳作的结晶,翻译即最高层次的外国文学阅读。
翻译之于创作亦有其不可磨灭的作用。好的作家往往也是翻译家,在中国,诗人柏桦即是将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稿作为他创作的开端。当年的“北大三剑客”海子、西川与骆一禾,将译诗视为与写作并重的事业。一部文学作品,翻译成其它文字,往往能得到些许别出心裁的闪光点。
沉浸于静谧的吐纳,亦能在其中找寻到数量可观的研究理论,这本书同时也是一部精致的文学理论导读。例如本书第三章《哈姆雷特和双重人》引出文学作品中的“双重人”概念,这一概念被后人借鉴的例子不胜枚举,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双重人“既是他用来再现生活、隐喻现实的一种策略,是他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一种美学手段,同时也可能是他自我意识的一种投射”。巴赫金由此再引出小说主人公和小说作者的对话理论关系,从而引出“复调小说”之文学结构。第四章《〈堂吉诃德〉与笑文学》中引出巴赫金的另一理论,即对狂欢化的“笑”复杂本质之研究,这是为文学研究者展示的另一条思路。第九篇《〈尤利西斯〉的现代性》亦是向读者揭示文学现代性的奥秘,即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体现出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即对民族宗教的反叛,“我不侍奉”即是现代性的体现,甚至是现代性本身。现代性在极大程度上拓展了文学的边界,亦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此外,书中的种种文学专有名词亦可依托作品继续挖掘,例如“意识流”“互文”等等。十一篇讲稿对文学理论的讲解深入浅出,将初识文学的学生引入文学研究的殿堂,亦为资深的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还为所有人留下了一些充满间性的思索——不仅是文学内部不同体裁的间性,还包括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建筑、文学与历史、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哲学,甚至文学与人类文明的间性,这些间性,亦是现代性的体现。
我们或多或少已感知到当下俄语文学的逐渐式微,这或因多年以来,人们对俄苏文学的刻板认知,抑或因为很多人认为从经典作品挖掘新意愈来愈难。作为国内俄语文学的资深研究专家,刘文飞教授仍然能从重读俄语文学经典作品中挖到新矿,亦如纳博科夫所言“一位好的读者,一位大读者,一位积极的、富有创造力的读者,就是一位重读者”。刘文飞教授本人的重新审读,在本书中的精彩体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他突破文学本身的思维定势与研究模式,将文学提升至思想与哲学的高度。例如陀氏的思想小说展示思想形成的过程,亦揭示思想自身的复杂性。阅读陀氏思想小说的读者,亦是向他笔下的思想家主人公学习思维的方式和思想的能力。阅读陀氏跨至文学之外的思想哲学,无疑需要重读再重读。
一门世界文学的课程浓缩于这本两百余页的书册。类似的讲稿集亦有问世,为读者熟知的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刘文飞教授在书中多次援引纳博科夫的观点,或是对《文学讲稿》的致敬。纳博科夫的讲稿使读者们认识到“作为艺术手段之一的语言是多么地丰富,又是多么地富于变幻,具有多么复杂的功能和可以开掘的表现形式”。本书引导读者认识到吐纳之间的文学外延,从神话、历史与文学交织的荷马,到文本、思想和哲学交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到诗歌、小说与评论交汇的纳博科夫。
世界文学名著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呼吸着多重空气,历代的读者们亦如曼德尔施塔姆对阿克梅诗派的定义:对世界文化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