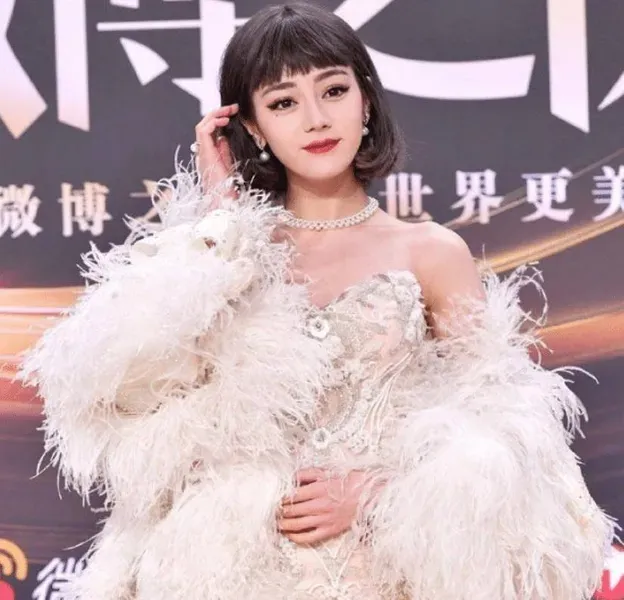看来郭德纲今年注定是风波的一年了,自从郭德纲公布家谱,广大吃瓜群众分分在曹云金何云伟微博贴吧里监督他们,把名改了。许多天没有动静的曹云金忽然发了条微博,对老郭一顿讽刺,说他一贯“含沙射影”对他们“赶尽杀绝”。
无独有偶,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娱记王小鱼也曾经曝出猛料。无图无真相,即使有99%的可能也是没有证据!不知道事情发展下去郭德纲会落得怎样一个结局!
德云社两成员离去,德云社停演,德云社被查,郭德纲背上了“三俗”的名号?反三俗=反郭德纲?郭德纲如何自处?围攻郭德纲的人如何自处? 反郭德纲者,娱记王小鱼的猛料就是事实就是真相,这位娱记可真得劲揭开了郭德纲这披着羊皮的狼!
反郭德纲者,娱记王小鱼的猛料就是事实就是真相,这位娱记可真得劲揭开了郭德纲这披着羊皮的狼!
挺郭德纲者,娱记王小鱼的猛料就是落井下石就是污蔑,这位娱记满口喷粪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啊!
我们不知道娱记王小鱼的猛料是真是假,不过不难猜测娱记王小鱼猛料的动机:
一,挺被打朋友,本是同行,又是朋友,两肋插刀实属必然,义愤填膺,口无遮拦!
二,无风不起浪,众人皆知娱乐圈乱,潜规则横行。大腕睡美女又如何呢?
真相如何,口快的郭德纲肯定会站出来!即使不是的话,郭德纲的“污名”也洗不干净了,雁过留声嘛!不管真假,各论坛的众网友已经开始猜测是哪位女主持了?
9月5日,曹云金再发长文,隶属郭德纲数宗罪行,表示自己知道太多郭德纲见不得光的事,例如某个曾跟着他的女记者。
曹云金在文章中表示,当年跟从郭德纲学艺每年交小一万块的学费,每月还要交500饭费,500生活费,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曾给郭德纲洗衣服做饭,养狗沏茶买菜做家务。2003年没来得及交钱,曾被赶出门,致使自己在公园的长椅上睡了一个星期。
曹云金还表示,因郭德纲的缘故,自己许多演出、推广也进行的不顺利。如10年曹开办的个人专场,因郭德纲跟场馆人打了招呼,导致演出受阻;11年曹在北展办演出,郭德纲暗中阻止舞美团队装台;13年天津春晚,郭德纲也和导演组打招呼“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名字是张文顺起的 不会改
提到最近网友呼吁曹云金改名字的问题,他表示,名字是张文顺先生给起的,张文顺用“云”字给大家做名,是希望“德云同在”,可惜郭德纲“德”没有了,但自己的“云”还在。
曹云金长微博全文:
二零零二年,你号称办学授课,我只身一人,满怀希望来北京求学,你说学期三年,学费每年8000,毕了业给艺术文凭,我那时初来乍到,又酷爱相声,便决定留下来随你学艺。交完学费后,你还给我开发票,签字盖章,母亲才放心把我交到你手里。
来了之后,我才发现,你这儿根本没有什么学堂教舍,是住家教学,除了每年交小一万块的学费,每月还要交500饭费,500生活费,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你总跟人说,有的徒弟是儿徒,从小养在家里长大的,我不知道谁是,反正我不是,你还记的吗,那时候家里就咱俩人,师娘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你的生活也拮据,我在你家,给你洗衣服做饭,养狗沏茶买菜做家务,学艺三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不觉得自己苦,初来学技能,本应如此。但我念的是我妈苦,她一个人在天津辛苦赚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攒下来的钱都供我学艺。可零三年的某个月,没来得及给我交饭钱,你便把我从家里赶出去,我足足在公园的长椅上睡了一个星期,要不是何云伟好心,把家里的储物间腾给我住,我真觉得那时候,我快坚持不下去了。我记得我们俩大包小包,带着我的锅碗瓢盆,他帮我搬家,我们没钱就没法找搬家公司,坐着819的末班车,盲流似的,奔向那个一个月350块租金的小房间,但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在北京又有了安身之所。就这么过了半年。
半年之后,你搬到大兴枣园,1500元/月的房租,你负担不起,又找我分担,你说你出1000,我出500,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把钱如数交上,又回到你家里,谁知好景不长,因为琐事你不高兴,再次将我赶出家门。万幸我又得到张德武先生的无私帮助,免费住进他的画室,那是一间地下室,由于阴冷潮湿,住在那里的岁月,我身上长满湿疹,白天出去练功演出,晚上回来桌面上就长了一层绿毛,吃的也存不住,经常回来以后,留好的食物都发霉了。但在北京可以有免费的住所,能够生存下去,挺好,我知足。尽管受了不少苦,我也没在意,谁学点本事不得吃点苦,我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
我知道那时候,你不看好我,觉得这些个徒弟里,我最不可能学出个名堂来,你给何云伟念《口吐莲花》,我连在旁边听的资格都没有,你们进屋关门,我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掉眼泪,我跟我自己说:“没关系,你自己好好学,以后你说的比谁都好,他终究会高看你一眼。”是的,我仰慕你的才华,论艺术方面,你有过人之处,我愿意跟着你学本事,我觉得,再苛刻的条件无非是一种历练,我希望我努力了,能得到你的认可,观众们喜欢我,我就成功了。
学艺三年,期间拜师,你从我的“姐夫”变成我师父,你说我和何云伟,每个人要交3000块拜师费,这是规矩。后来你觉得3000要少了,琢磨这事儿还能赚钱,你让我和何云伟,统一口径,告诉潘云侠拜师费是5000,这样你又能多赚2000。
随后,我在德云社足足效力了五年,这五年我自认为无怨无悔,任劳任怨,从来没跟谁抱怨过。生活里,对师弟们,我毫无保留地带他们使活,把我会的都念给他们;舞台上,所有演出我认真对待,除非伤病,基本场场不落。
团队如日中天的那两年,公司没有社保,我一个月演满了,32场演出,到手的工资有四千多,当时觉得,一群人在一起为了一个目标努力,为了大家更好,值得,一场一百多也没什么。我实实在在的觉得这个团队不容易,我有感情,我也年轻,从没觉得是吃亏,苦尽甘来,吃亏是福,以后还能挣呢,那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
可后来,这种一团和气,共同前进的氛围在不知不觉中,变了。零六年我参加CCTV相声大赛,一路过关斩将到决赛,决赛是直播,大赛给了我18分钟,让我好好表现,可在直播的前一天,你告诉我:“退赛!”我问为什么?你说:“没有为什么,我让你退,你就得退。”我没办法,总导演气得摔了电话,师爷侯耀文先生打了两个小时候电话问我是不是疯了:“你这么不负责任,以后,谁还给你机会?”我只能说:“师爷,我没办法,您得和我师父说,您是他师父,我是他徒弟,有一句话说的好,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这是我的处境。”我还记得,师爷最后冲我嚷嚷了一句,:“他不接我电话,你们要造反!”之后也摔了电话。最终,这个事件以你勒令弟子退出央视相声大赛的新闻,铺天盖地而告终。我后来才明白,我可能会因为退赛失去央视这个平台,遭到封杀,你以后好控制管理,我再想出头就难了。
但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失去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我没气馁,继续安心演出。零七年你拍《窦天宝传奇》在天津拍摄三个月、一分钱都没给我,我要求尽量保证北京小剧场的演出,想尽一切办法赶场,因为拍戏没钱,演出有钱,我得赚钱,我得填饱肚子,一场演出150,我不敢落下,为了赶演出,我要自己承担油钱,来往的过桥过路费,最后一算,我还是赔了好几千。
零八年天津开分社,演出费低,没人愿意去演,我带队开专场,一场卖出十几万票房,我就拿着500块演出费,过路过桥费还是一律自付,不管吃不管住,演完赔钱这么干。晚上十一点多演出结束,我得连夜返回北京,因为,第二天下午北京还有演出,我当时没别的想法,就是挣钱,因为我得活着。
零九年拍《三笑才子佳人》,上海拍摄近两个月,也是分文没给,这回连演出费都没的赚了,就这么零收入生扛了过来;你总说你在钱上没亏欠过任何人,拍戏没钱,是因为片子没卖,所以不能给我片酬。我想不明白,我又不是投资人的身份,为什么要与你们担卖片子的风险?我在你那,连合作都谈不上,就是一个雇佣关系,为什么我演了戏,付出时间、付出了劳动,连养活自己的工资都没有呢?平心而论,没有收入,我真不知道靠什么活。你也穷过,你应该知道活不下去的滋味。最不能理解的是,后来片子播了,影片也上映了,这笔钱也没补还给我,这就是你对谁都毫无亏欠,是这样么?
也许在你眼里,你从没错过,回顾你出道以来,你先骂授业恩师杨志刚,捏造人家挪用公款,后来你转拜相声名家侯耀文,又骂李金斗、再骂姜昆、骂冯巩,几乎把中国声界骂遍了,你说相声圈里没有一个好人。尤其骂姜昆的时候,你强制要求所有在团队的人,都要发文开骂,我们不愿意,你说:“不写以后没演出排给你,以后别想挣钱。”你不断的威逼,要求徒弟们,要不断的表忠心,说你各种好,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他们有心想走的时候,再说你的不是,也无从说起吧?
你还骂相声大赛,说里面肮脏黑暗,骂央视春晚,发誓一辈子都不会登那个舞台,但是到了2013年你还是上了春晚;你代言的藏秘排油被曝光,你骂中央电视台315晚会;你侵占绿地被曝光,所以辱骂北京电视台;你打完记者,骂记者不如妓女;你抄袭段子手的作品,人家找到你,你骂他们是来“碰瓷”的,还拉黑他们。有质疑你的观众,你当然也没饶了他们。所有人,都是你想骂就骂,想打就打。相应的,你也赢得了一轮又一轮的舆论争议和炒作,你不断登上热门新闻话题。
观众们喜欢你的艺术,粉丝们喜欢你的作品,你以弱者之姿,行敢言之态,收获着他们对你的支持和爱护,所以轻易地,你也煽动了他们,利用这些喜爱之情,跟着你,对那些“敌对势力”诅咒谩骂、口诛笔伐,几场仗干下来,你没受过挫,所以你越战越勇。
直到有一天,你突然给刚刚因病离世的北京台台长王晓东贴红喜字,写打油诗,逞口舌之快,这一仗你触碰了人们的情感底线,作为一个艺人,连死去的人都不放过,何况他与你的人生毫无瓜葛,所以第一次你吃了大亏,不得不收敛,低调了好一阵。其实我一直想问,难道一直以来,这些所有的事情,所有你骂的人,都是因为你对?别人错?世人都对不起你?你无辜至极?
你接受采访,告诉所有人,当今社会险恶,人心叵测,人人都有一颗阴暗的心理,你关闭评论,说评论你的人都不怀好意,可是为什么世上好的一面,你就看不到呢,也从来不鼓励,只一味强调记仇念恨、睚眦必报的手段,究竟是意欲何为呢,你到底在宣扬什么?
二零一零年,所谓“八月风波”,你四处哭诉,一行人在你危难时刻离去,背弃了你。可实际上,我当时毫无离开的想法,只是对你们合同的条约心存疑虑,在与你商量,得到你允许的情况下,暂时没有签约,你跟我说:“金子,任何时候,任何一家剧场,你都可以演出,这是你的特权,也是我对你的承诺。”我当时也对你说:“家里任何演出,我分文不取,这是我对你的回报。”
九月,你安排的团队自查结束,一切回归风平浪静,我依然在团队正常演出,然而,到了10月中旬,我却突然遭到禁演,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演出部”禁止我登台,为此我到处找你,沟通无门,直到十一月,失去舞台的我,才意识到,之前没有签约的行为导致我自己可能已经被赶出来了。可是我没签约,你是亲口同意了的啊?你忘了么?
十一月底,我寻找到新的舞台,仍然没有放弃缓和你我之间的关系,试图与你取得联络,你却关紧了所有的大门,我只能抱着一丝幻想对来看我的观众说:“我没有离开,你永远是我师父。”我总觉得,过几天,只要咱们见着面了,把事情说开了,我们还是会坐在一起,笑骂几句,这事儿就过去了,人生么,谁们家还没有个矛盾不快呢?做人阳光一点,想开了就完了。
结果,我没等来和你见面,是我想简单了,转眼到了二零一二年底,某次活动中,你突然对媒体说:“曹云金,我没法评价,他走了三年,我没有收到过任何一个短信,也没见过人。”当时在山东临沂拍戏的我,被前来探班的记者问得一头雾水,我几乎是不敢置信地拿出手机给记者看,三节两寿,你有大事小情的时候,我都有给你和师娘发送的问候信息,师娘也都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