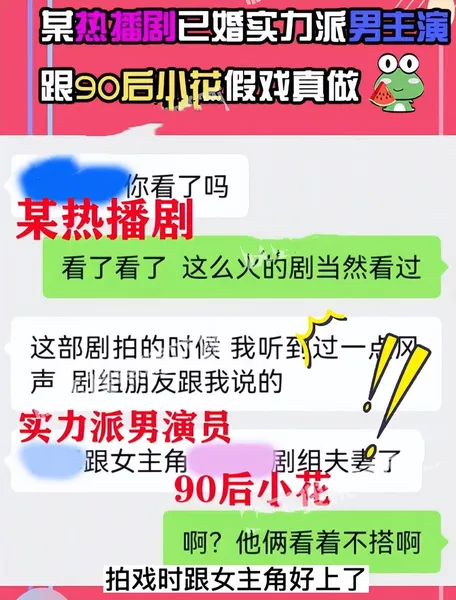嗵嗵,大门被擂得直响。汪婉儿穿上端木春生媳妇留下的衣服,又用一块破布蒙着头,急着跑出家门,忙说:“来了,来了。”她打开大门,端木春生担着一担水,跨进大门。端木春生抬头,一下愣怔住了,眼前的汪婉儿,分明是换了一个人。她脸面白皙,两眼大而黑,又是重眼皮儿,鼻梁微挺,嘴唇适中,不薄不厚……穿着他女人的衣服,也挺合身。他一直盯着汪婉儿,两眼直愣愣的。汪婉儿脸面红扑扑的,低头,说:“大哥,这有啥好看的……”端木春生把水担回家里,又倒进水缸里,转身,看着汪婉儿,十分欣喜,那眉眼里都泛着笑:“嗬,都洗过了,家里也亮敞了。”汪婉儿像是有啥歉疚的,说:“大哥,我只顾给娃儿们和我洗了,还未做饭……”端木春生摆手,说:“哎,不忙,你们初来乍到,也找不到个头绪。”他把水桶、担杖放出窗外,回来,看着汪婉儿,又说:“咱吃粥吧。”汪婉儿点头,妩媚一笑,说:“大哥,我来。”她又舀两勺水,倒在锅里,看一下,说:“大哥,够了吧?”说罢,她从地上的筐里拿起几颗山药,在一个小盆里洗净,看着端木春生,说:“大哥,旋山药皮吧?”端木春生忙说:“旋,旋!哎,婉儿,别左一个大哥右一个大哥,以后一个锅里搅稀稠了……”他停住了,看到汪婉儿脸上一层羞赧,又忙改口:“嗨,我嘴上缺个把门的,你别在意。”
粥饭熟了,窑里弥漫着香气。端木春生把粥饭盛在两个碗里,首先递给两个孩子,关切地说:“吃吧。对,放开肚子吃,你们一定饿了。”他又给汪婉儿盛了一碗,递上,一笑,说:“端上,你也得多吃一些。”尔后,他自己盛一碗,蹲在地上,吃了起来。汪婉儿心里十分感激,看着两个孩子,说:“愣着干啥?快吃!以后,有你叔了,咱们有个遮风避雨的了。”她又看着地下的端木春生,说:“大哥,我们娘儿三人,给你带来麻烦了。”说毕,汪婉儿跪下,是要给端木春生磕个响头。端木春生忙着站立,把碗放在锅台上,扶住汪婉儿,说:“不敢,不敢。婉儿,你不晓得,我也是个苦命人……”说着,眼里也湿润了。汪婉儿站起,喉管被塞满了,一再哽咽,说:“大哥,你收留下我们娘儿三人,我感激你啊。你若不嫌弃,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妻子,两个孩子也就是你的娃儿。哎,我没有别的,讨吃几年,只攒下七个银圆,在箩头里。”端木春生听了,哦声,说:“难怪你把箩头抱得紧哩。婉儿,我不要你的,你自个儿拿着,将来,是有用的地方。我一身力气,能养活你们娘儿三人。”汪婉儿看着端木春生,想,七个银圆,他也无动于衷?按说,村里穷人听到有个啥,是一定要看看……端木春生拉着汪婉儿朝东窑走去。“嘿,你不晓得,东窑几个囤里都堆着粮食,是够咱们吃的。”汪婉儿听了,毫不掩饰,说:“我在这儿洗身子,是看到了。”他俩到了东窑,端木春生望着汪婉儿,有些手足无措,说:“你看到了,也好。这是你的家了,一切也是你的了。”汪婉儿一下扑在端木春生怀里,两臂抱着端木春生,动情地说:“大哥,我是你的了,你想咋就咋……”端木春生搂着汪婉儿,亲吻一阵儿,说:“婉儿,等晚上吧。前晌,我还得到地里去。再说,你洗的这样干净,晚上,我也的洗干净呀?不然,那不是糟蹋你了?”汪婉儿把端木春生搂得更紧了,望着端木春生,那心里的激情,像一泓流水。端木春生抚摸着汪婉儿的头发,诚恳地说:“婉儿,我们在一搭不是十天半月,日子长着哩。相信我吧,我不会让你们娘儿三人受疐的。”汪婉儿抬头,眼里模糊了,说:“大哥,我相信你!”
端木春生上地里了。家里只有汪婉儿娘儿三人。男孩睁着黑黑的眼睛,看着汪婉儿,问:“妈,以后,我们就在这里了?那人我俩得叫爸了?妈,这人生得有些像我爸的。他要穿上我爸的服装就更威风了。”女孩嘘声,悄然地说:“哥,这里人不叫爸的,人家叫达。”汪婉儿听了,盯着两个孩子,一再叮嘱:“对,从今往后,他就是你俩的父亲了,你俩就是农家子弟了。你俩在村里,一切得像村里孩子一样。你们说话做事,都不能有个闪失。记住,我们是从安徽逃荒来的,什么县,什么村……哎,是啥县,啥村,我不是几次说了?”两个孩子点头,说;“妈,我们记住了。”“妈,你别为我俩操心了。”汪婉儿思忖一下,抬头,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千万不能忘啊。”男孩知道,刚才把话说错了,啥“穿上我爸的服装就更威风了”,不,我爸死了,是二十八岁时死的。
晚上,两个孩子酣睡了。在一床破被里,汪婉儿让端木春生尽兴地享受了一次快乐。端木春生抱着汪婉儿,低语:“婉儿,你身上真香啊。有你给我暖被窝了,也满足了。”汪婉儿十分动情,说:“大哥!”端木春生把她嘴捂住了,拉起被子,埋住头,才说:“村里有个习惯,男女圆房,他们都会爬进院里,在窗下偷听。”那被子散发出的气味,是让汪婉儿有些窒息,挺难受的。她憋着气,听端木春生说着,尔后,把头露出被子外,呼吸一会儿。端木春生有些歉疚,说:“你受不了这气味吧?明儿,你拆洗一下。”汪婉儿把头杵在端木春生胸前,说:“行。哎,你咋没娃儿呀?”端木春生迟疑一下,说:“我也不晓得咋的。我和她一搭五年了,可她老也怀不上。她吃了十几副汤药,也不抵事。”汪婉儿听了,说:“大哥,我看也不一定是女人的毛病,有时,是男人的毛病,男人也有不生的。”端木春生想了一下,说:“对,有这种事儿。哎,婉儿,你知道的挺不少啊。”汪婉儿心里一惊,掩饰地说:“大哥,你夸奖我了。其实,我也是听一个医生说的。我身上的刚走几天,不定,我会给你生一个呢。”端木春生欣喜地说:“那太好了……不过,有你两个孩子,我也知足了。哎,别老叫我大哥。你把身子给我了,我是你男人了。我还没问,两个孩子叫啥?”汪婉儿思忖一下,说:“村里人嘛,起个名字也是狗儿呀猫儿呀。我来这里了,两个孩子也是你的孩子。我看……男的就叫端木顗,女的就叫端木訸……”端木春生听了,说:“对,端木义、端木和这挺好的。”汪婉儿知道,端木春生一定不晓得顗、訸。她也不去更正,以后,等孩子念书了,再说。她抚摸着端木春生的胸脯,像有啥心事,犹豫一下,才说:“大哥……春生,你说,两个娃儿总得认几个字啊?等过几天把他俩送学堂吧。”端木春生听了,不假思索,说:“咱村里眼下还没有学堂,那榆洼沟村是有的,不过,离咱这里有十几里路……俩娃儿跑来跑去,是不放心。你也知道,狼是不少……”汪婉儿轻柔地说:“春生,让他俩住学堂嘛。”端木春生清楚,刚同汪婉儿结识,也不摸底细,说:“那得花多少呀?咱能拿得出吗?再说,这霞石村也没有几个念书的,俩娃儿上学堂了,也太显眼了。”汪婉儿把端木春生头扳到她乳沟上,拉起被子,在他身边说着。端木春生听了,也不感到惊愕,平静地说:“这是真的?这下,一切都不愁了。行,让端木义、端木和到榆洼沟村学堂去。”汪婉儿一颗悬着的心,一下踏实了。她摸着端木春生的下身,说:“春生,你能行吗?”端木春生一听,有些激动,说:“我早想哩,我是怕你太劳累了,不大喜善……”
那天,是个后晌,端木春生赶着一头黑灰毛驴,去榆洼沟村接端木顗、端木訸。两个娃儿已在榆洼沟村学堂有一个月了。汪婉儿十分想念。早上,汪婉儿对端木春生说了,也不晓得顗儿、訸儿咋的了?虽然汪婉儿没有直说,可是端木春生听明白了,汪婉儿是让他抽个空隙,到榆洼沟村把顗儿、訸儿接回,同父母团圆的。端木春生从圈棚里拉出牲口,是要到井台上饮去。他站定了,看着汪婉儿,一笑,说:“行啊。后晌我接他俩去。”汪婉儿拿块抹布,在门口两手拍着,俨然像个家庭妇女,听了,盯着端木春生,停一会儿,才说:“春生,你回家里,我有话要对你说呢。”端木春生把驴、牛牵出大门,又把驴、牛缰绳在大门外的石柱上紧牢,返身,回到了院里。汪婉儿把他让进家门,而后,又把家门闩上。她回到西窑,看到端木春生从口袋里掏出旱烟杆,忙着从锅脖里拿过火镰,啪啪打着,将燃着的布格英绒丝递上,端木春生把燃着的布格英绒丝按在旱烟锅上,猛吸几口,看着汪婉儿,说:“你说,有啥安顿的?”汪婉儿看看端木春生,把他褶皱的上衣揪一下,抬头,眼里闪着柔光,说:“你到学堂了,人家先生一定会盘诘的,你两个娃儿天赋、悟性都不错的,哎,就是他俩从小挺聪明的,先生一说他俩就懂得了……”端木春生吸一口烟,吐出,说:“婉儿,我对你说几次了,我都晓得呀。”在端木春生说时,汪婉儿抬手,扇着烟雾。端木春生抬脚,在鞋底上把旱烟锅一磕,笑着,说:“烟太呛人。以后,我不抽了。”汪婉儿有些埋怨,说:“你别觉得不耐烦了。不管到了哪里,都得留心……”
(未完待续)
A
编者按
1度,打造原创情感故事,碰撞经典影视影评,倾吐喜怒哀乐心情,直抒小诗美文情怀!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分享你的芬芳馥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