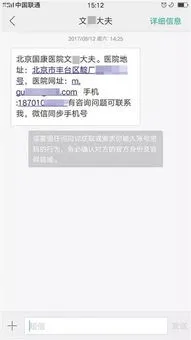本文转自:人民日报客户端
孙海天
(相关资料图)12月22日,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奖」入围剧情长片《巨人》在三亚1+X红树林影城举行展映。放映结束后,导演黄然出席影片映后见面会活动现场,分享创作经历。
《巨人》讲述了一个具有悬疑色彩的侦探故事。20世纪90年代,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家精神病院,一个名为马德斯·莱克的人供认了多起谋杀并因此被定罪。然而,马德斯、治疗师安娜·鲁德贝克和警察索伦·兰克三人都在挖掘真相的获益。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他们不断加深的共同利益关系正在悄然反噬三人。
作为导演黄然的首部剧情长片作品,《巨人》有着很强的国际视野,它也是爱奇艺影业出品的首部国际影片。影片集结了一支跨文化的创作团队,主演是北欧演员古斯塔·斯卡斯加德,摄影指导是美国摄影师克里斯·布劳维特,音乐来自澳大利亚音乐人班·福斯特,导演黄然来自中国,而取景地则选择在芬兰。
在冷峻的摄影风格下,影片看似在追问悬案背后何为真相,实则探讨了人与人之间最隐秘的情感需求。嫌疑犯、治疗师与警察之间的利益关系转为一种去身份化的过程,三人逐渐展开对自我精神的直视。时而虚焦的镜头模糊了现实的清晰棱角,走入真相的灰度地带,让观众沉思生活里的暧昧与无解时刻。导演相信,相对于非黑即白,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存在于灰度之中,追寻答案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巨人映后Q&A
王垚:这是一个在芬兰拍的英语片。
黄然:因为语言的原因,芬兰的英语非常普及。我希望这是一个平行的电影,并不想把它拉到芬兰本土而强调背景。对我而言,我始终是一个外来者,要说我对这个本土故事有多了解,我自认为比较了解,前后七年做下来这个项目,你又说我很了解也没有,我很尊重这种距离感。
黄然:至于芬兰,我选择这里有很多原因。第一是关于场景,我们看到的那个医院。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这个医院不是想象中有铁栅栏的医院。在90年代精神病院,他们认为精神问题是社会问题,不是个人问题,他们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病患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模糊的。影片中的医院就不是一个铁栅栏医院。我当时在网上做调查时就找到了芬兰这个医院,它是芬兰最有名的一个设计师所设计的,有100年的历史。我当时觉得在网上看图片特别符合我想要的医院的样子,在一个森林里,后来实地看过后觉得特别符合。第二是电影从故事发生地转去芬兰拍是很贵的,所以我们围绕着这个医院扩大,先在那个城市看看有没有更多适合的场地,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后来想,是不是可以在赫尔辛基看看有没有符合我们想象中的场景可以用,最后慢慢就变成了100%在芬兰拍了。
王垚:我还算了一下时间,应该是1993年到1998或1999年的故事。
黄然:对。
王垚: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请您谈一下真实事件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事件,您做了什么样的改动,它给了您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去做这样一个故事片?
黄然: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片。我之前是艺术家,虽然在当代艺术领域也拍短片,但是与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行业,语境也不太一样。虽然我很喜欢电影,但是在之前拍电影对我来讲是天方夜谭的一件事情。我在2014年有一个短片去了戛纳,认识了我现在的经纪人和制片人,他们就问我想不想拍第一部长片。想是想,但是我不知道拍什么,我也不可以一边当艺术家一边拍电影,在能力上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这意味着需要放弃很多。我当时就想等一等,就正式把这个想法放下了。
黄然:有一次在伦敦做展览的时候,我翻杂志发现有一个原型故事特别有意思,讲语言、性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我在当代艺术里关心的事情比较贴近。我第一个想法是可不可以基于这个事做下一个个展,跟电影也没有关系。但是我回到北京之后做了差不多半年的调查,我慢慢发现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容器,或者一个语言,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最佳的媒介,反而那时候电影的概念慢慢成型了,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权衡了一下,决定做第一个长片。
黄然:这部影片我做了很大程度改编,因为这件事是当地每个人都知道的案件,跨度时间比电影更长,有20年。在20年的时间里能说的都说完了,大家最后定义这是他们司法体系上最严重的一次误判。对我来讲,我不想拍一个社会性事件,我不是把人简化到黑与白。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向做的话,最后所有人都会简化为黑与白,像卡通人一样。而当事人并不会面对采访具体讨论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所有知道的事都是表面上的。后来我想更多关注背后可能发生什么,开篇也说了不是基于原型事件改编,而是受原型故事启发。因为改编程度很大,可能接近80%,因为一个人如果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困在其中,并没有人强迫他做这件事,其实跟真实与否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更多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需求。
王垚:还有一个问题,做艺术家、做短片是白河里,做电影是黑河里,一般意义上你对当代艺术创作和电影创作有什么不同的理解?
黄然:短片在当代艺术里是很完整的东西,首先你没有那么多钱拍一个长作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所以很多艺术家会争取在一个短片的结构里做出比较完整的东西。这样叙事或者故事本身又不会和电影那样有这么强的关系,很多时候更多是强调观念上的尝试和创作。转到电影,电影根本上是关于故事本身,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艺术品有的时候是强迫你去观看,电影是有选择的,你不需要强迫谁去观看。很多时候会在观影之后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回到你的个人经验里,这是非常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当代艺术里很多时候会过分强调一个媒介对于人的影响,很多时候电影给你一个更自由的环境。
王垚:我们还有点时间,开放现场的问题,哪位观众想跟导演聊一聊?
观 众
黄老师好,我想跟您聊聊电影一些具体的构想,比如您的转场。我发现您特别喜欢用黑场转场,但是黑场之后通常接一个定场镜头,不带任何建筑的外景,再接一个内景,把镜头画面带到建筑内开始室内戏。对我来说这种处理对我造成一种观感上的割裂,不太能接受,我想问问您为什么这么处理?
黄然:这个电影它的台词量也算挺大的,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节奏并没有那么密集。其实影片有一半是在处理沉默,有一半在处理语言,处理沉默那部分给的信息并不那么清晰,这也是跟整部电影的概念相通。所以,不管是摄影上,还是声音上,大家都是在一个平行的方式上处理沉默,你看到很多转场是故意做到完全静音,因为这个电影并不是那么容易观看。很多时候如果把它粘起来的话可能觉得很累,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呼吸点,那个呼吸点可以通过声音、画面处理另外一种方式的沉默。
观 众
既然说到节奏,您对整个影片的节奏和段落是怎么想的?在我看来,您选择的题材如果处理成偏类型的节奏肯定更吸引人,但是您选择了这样一种比较缓慢的文艺片的节奏,我感觉是题材和您影片本体的节奏有对立。这个对立延续到了后面,让我感受到了一点类型片的气质。男主在掐心理咨询师的戏,那个点是有起伏的,有点类型片带来的激动感,在这个激动劲上来之后又平静了,回到了文艺片的节奏,感觉像是有一点突起,但是又没有完全突出来,您对整个片子的节奏是怎么想的?
黄然:这个事件本身如果说是类型片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做非黑即白他到底有没有杀人,看到最后这个答案重要吗?或者你已经有了答案。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黑与白之间是一个灰度,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生活在灰度里。在影片里,不管是摄影语言上的重复,还是特别小的点不断地重复,我希望通过这些塑造一种重量,每个人的人生灰度的重量。这部分的东西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里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就像你说类型片很多时候在找答案,但是塑造人生时很多时候是没有答案的。可能跟你想的有所差别。我创作的出发点为什么抛开黑与白的东西,是因为我想讨论的是灰度,而这个灰度肯定没有黑与白的起伏那么大,但是灰度肯定有重量。像这种题材之前已经看到过,比如《聚焦》。《聚焦》就是黑与白,对我来讲,这样的电影太多了,而且里面的人特别像卡通人。
观 众
您讲的黑白是一种立场吗?
黄然:不单单关于立场,也关于人本身,因为这里面很多信息可以被感觉到,但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
王垚:观众问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WHAT REMAINS》和《巨人》之间的翻译差距还挺大的。
黄然:《WHAT REMAINS》比较抽象,翻译过来是"还剩什么"。而中文名《巨人》有两方面的原因,在北欧神话里有很多神,所有的神都是从巨人的血液里滋生出来的,所以在北欧神话里巨人是混沌的状态。很多时候人生大部分是灰度,两者间有某种接近的地方。另外一个层面,这三个人其实是社会的边缘人物,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差。
观 众
导演好,挺喜欢您的这部片子。我有点好奇,女主跟父亲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是不是也被父亲虐待过,看到她的父亲有点问题。
黄然:在电影里暗示了很多,但是这个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谎言与真实的边界在这个电影里是很模糊的,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为什么把一个社会性的事件浓缩到三个小人物上。其实有一个带引号的家庭关系,你一旦把很多事放在家庭关系里,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不是绝对的真实,我们的真实建立在彼此的情感需求上。所以可能你也感觉到了,最后他的哥哥说“不确定”,那个理解是非常复杂的,你可以认为是也可以认为不是,但我没有答案。
观 众
导演好,我是在您的电影中发现了这样一对张力,一边是律法方面的张力,另一端是人性向善的一面,包括在耳机中放了三次"追求人的灵魂积极"之类的。可能这两个张力是相对的,感觉你的片子也是在这样的张力中运作。所以想请教一下导演是怎么看待这对张力的?它和您的片子有哪些关系?
黄然:我可能没有这么具体想过这个张力,三个人在生活里都有缺失的点,这个事件把三个人联系起来了。电影里有一场戏,女医生安娜·鲁德贝克第二次跟导师坐下来讨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细节,他们第一次谈话我用了两个全景,几乎没有任何特写;第二次是一个叠加的特写,安娜·鲁德贝克说想创造一个完美的童年,她的导师说“完美可能是生活里没有答案的那部分”。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追寻的答案到最后是没有答案的,正是没有答案的过程让你的人生变得很重。
观 众
我想延续一下刚才的问题,您更想在这部作品中寄予这样的人文情怀,探讨人生灰度的部分。在电影搜证追寻的过程中,人文情怀处于律法的枷锁下会带着枷锁跳舞。我想问一下这部电影是怎么构思的?在律法与人性向善的创作上,是如何带着这种枷锁去跳舞的?
黄然:我觉得你形容得特别美,我创作的时候没有想"带着枷锁去跳舞"这么有诗意的形容。在90年代,那里的人工受孕是不合法的,很多人去丹麦。丹麦有世界上最大的精子银行,你可以去挑什么颜色的眼睛、头发、肤色、高度,你肯定看不见这个人的容貌,但是可以听一段他的录音。电影里的录音是真实的。我不觉得录音内容是人心向善,我故意把它处理地像一个机器,过于美好但特别不人性。为什么这个病人一直去听,我觉得有吸引她的东西。回到你的问题,也是类似的,不可能有答案这种东西,但是我们会不停去尝试和寻找答案。最后有没有答案不重要,探寻答案的过程倒是挺重要的。
观 众
你拍摄了一个真实发生的有20年跨度的凶杀案,除了凶手和调查方,还有受害者家属。受害者家属在电影里并没有出现,这是不是刻意淡化?目前拍摄凶手、杀人犯改编的电影很容易招致伦理上的批评,我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发现缺失了这样的反馈,而这个电影一直在处理三个家庭的关系,调查人、嫌疑人、心理医生的关系,您在处理的时候是故意不去讲道德审判而只关注嫌疑人的心路历程吗?还是有别的关注?
黄然:这个故事最后落到了病人身上。也是借用电影里的一句话,其他人都是搭便车的人,特别是警察,这辆车其实是医生和病人在开。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些,我相信大家看到最后,虽然没有人点破这个事实,我相信大家99%都相信他从来没有杀过人。这并不是基于连环杀人案所做的故事,那些受害人跟他没有关系,这部电影只是在讲他的人生和那两个人的人生。
王垚:感谢大家留到这么晚,谢谢导演,预祝《巨人》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取得好成绩,谢谢大家!大家晚安。